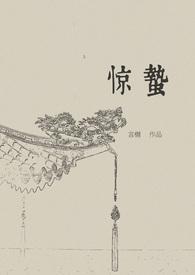无线文学>重生改嫁,前夫娶白月光悔断肠 > 第409章 阿依夏木(第2页)
第409章 阿依夏木(第2页)
陈大勇打头,戚何断后,林心萍走在中间。
他们用背包绳把三人连在一起,带上简单的干粮、水壶、指南针,以及那本至关重要的日记,在上午天色稍亮时,踏出了哨所的门。
下山的路,每一步都像是在与自然搏斗。
积雪深及膝盖,每拔一次腿都要耗费极大的力气。
风虽然小了,但卷起的雪沫打在脸上,依然像细针扎一样疼。
能见度很低,几米之外就白茫茫一片,分不清哪是路,哪是悬崖。
陈大勇走在最前面,用一根长木棍探路,每一步都踩得异常谨慎。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
戚何紧紧拉着连接在林心萍腰间的绳子,既要留意她的脚步,又要警惕身后的情况。
林心萍咬紧牙关,努力跟上陈大勇的节奏,肺部因为寒冷和缺氧火辣辣地疼,但她脑子里反复回响着郑卫国日记里的字句,那成了支撑她前进的最大力量。
短短十几里山路,他们走了近四个小时。
当看到扎西村那些低矮的,被厚雪覆盖的土坯房轮廓时,三人都不由得长长松了口气。
扎西村静得出奇,只有几缕倔强的炊烟从厚厚的积雪下钻出来,表明这里还有人生息。
陈大勇凭着记忆,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村子东头一户人家。
院墙是石头垒的,木门紧闭。
陈大勇拍打门板,用生硬的藏语喊着,
“卓玛阿妈!卓玛阿妈在吗?”
过了好一会儿,门才“吱呀”一声打开一条缝,露出一张布满皱纹,慈祥的藏族老阿妈的脸。
她眯着眼看了半天,才认出来人,顿时惊喜地叫了一声,连忙把门完全打开,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汉语说,
“陈班长?哎呀,快进来,快进来!这么大的雪,你们怎么下来了?”
屋里比外面温暖太多,一个铁皮炉子烧得正旺,上面坐着的大铜壶咕嘟咕嘟冒着热气。
浓浓的奶茶香弥漫在整个房间。
卓玛阿妈手脚麻利地给他们倒上滚烫的酥油茶,又端出一盘风干的牛肉和奶渣。
“先喝点,暖暖身子。”
卓玛阿妈关切地看着他们冻得红的脸颊。
喝下几口热茶,暖意从喉咙一直蔓延到四肢百骸。
林心萍这才缓过劲,拿出那本日记,说明了来意。
她翻到郑卫国描述阿依夏木的段落,指给卓玛阿妈看。
卓玛阿妈不识字,但听到“阿依夏木”的名字,又看到日记本上那些工整的汉字,眼眶瞬间就红了。
她颤巍巍地起身,走到里屋,翻找了半天,捧出一个洗得白,边角已经磨损的军用挎包。
挎包是军绿色的,正面用红线绣着“为人民服务”五个字,虽然褪色,但依然清晰。
“这个……是郑班长,退伍那天留下的。”
卓玛阿妈用粗糙的手指抚摸着挎包,声音有些哽咽,
“他说,他就要走了,没什么好东西留给夏木。这个挎包结实,留给夏木上学用,装书,装本子……”
林心萍接过挎包,感觉手里沉甸甸的。
她小心地打开,里面整整齐齐放着几本旧课本,纸张已经泛黄卷边。
课本下面,是一沓用粗糙的作业纸仔细订成的小本子。
她轻轻翻开最上面一本,扉页上,用铅笔笨拙地、一笔一划地写着四个汉字,阿依夏木。
后面的页面上,是简单的汉字抄写,
“人、口、手、山、水、田……”
还有用稚嫩笔迹完成的加减法算术题。
字迹从最初的歪歪扭扭,大小不一,到后面渐渐变得工整、规范。
可以想象,当年那个豁着门牙的小女孩,是怎样在跳跃的油灯下,趴在炕沿上,认真地书写着这些改变她命运的符号。
而那个即将离开的战士,又是怀着怎样的期望与不舍,留下了这些承载着知识与希望的物品。
“阿依夏木……她现在在哪里?过得好吗?”
林心萍的声音不自觉地放得很轻,生怕惊扰了这段尘封的温情。
卓玛阿妈擦了擦眼角,指向窗外更远的,被雪雾笼罩的山谷方向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