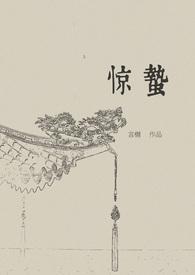无线文学>重生改嫁,前夫娶白月光悔断肠 > 第409章 阿依夏木(第1页)
第409章 阿依夏木(第1页)
那晚煤油灯下的长谈,像是悄悄推开了一扇窗。
战士们看林心萍的眼神,多了种说不清的信赖。
第二天一早,小赵磨磨蹭蹭凑到正在整理日记的林心萍身边,手里攥着个东西。
“林老师……”
他把手摊开,掌心是枚磨得亮的子弹壳,上面用刀子歪歪扭扭刻了个“家”字,
“这个,是去年我爹托人带上来的。我家穷,没啥能给的,我爹就把他当民兵时留下的这枚子弹壳给了我,说想家了摸摸它。这个……你能写进去不?”
林心萍接过那枚带着体温的子弹壳,郑重地点头,
“当然能。不仅要写进去,还要把你爹的话也写上。”
小赵的眼睛一下子亮了,挠着头嘿嘿笑,又跑回去翻自己的储物箱,想看看还有啥能贡献出来。
这天下午,林心萍在整理那厚厚一沓日记时,被一本年的日记深深吸引。
日记的主人叫郑卫国,字写得刚劲有力。
这本日记里,反复出现一个名字:阿依夏木。
“……年o月日,晴。阿依夏木又来了,小脸冻得红扑扑的,背着比她人还高的背篓,里面是她阿妈新打的酥油和奶渣。她汉话说得不好,只会冲我们傻笑,露着刚掉了门牙的豁口。我们教她写‘中国’和‘解放军’,她学得可认真,小手冻得通红也不肯放下笔……”
“……年元旦,雪。阿依夏木跟着她阿妈来送年货,偷偷塞给我一个用羊毛线编的手链,说是她阿妈教她编的,戴着暖和。这小丫头……”
“……年月,风大。阿依夏木说她想上学,可村小学太远。我们几个商量,以后每次她来,轮流教她认字、算数。班长说,这叫‘军民共建扫盲班’……”
日记在o年夏初戛然而止。
最后一页写着,
“……明天退伍。把剩下的笔记本和铅笔都留给阿依夏木,希望她能一直学下去。小丫头,要好好长大啊。”
林心萍合上日记本,心头沉甸甸的,又暖烘烘的。
窗外,暴风雪依然在呼啸,但她的心,已经被那个叫阿依夏木的藏族小姑娘,和那群可爱的战士,带到了几年前那个阳光和煦的午后。
“阿依夏木?”
正巧陈大勇路过,探头看了一眼日记本,
“我知道!山脚下扎西村的,她阿妈就是每年雪化后,第一个背酥油上来的卓玛阿妈!”
“那阿依夏木现在……”
林心萍急切地问。
陈大勇挠挠头,想了想,
“后来好像嫁人了,嫁到山外去了吧?有好几年没见着了。郑班长,就是写日记这位,退伍前那阵子,总望着山下呆,还跟我们念叨,不知道那小丫头还记不记得怎么写自己名字,算数有没有进步。”
一个念头,像雪原上破土而出的嫩芽,在林心萍心里顽强地扎下了根。
她想去找到阿依夏木,不仅仅是为了补全一段日记,更是想替那位牵挂的郑班长,看看那朵他曾经浇灌过的格桑花,如今是否安然绽放。
……
三天后,肆虐的暴风雪终于显露出一丝疲态。
风势减弱,雪也变成了细碎的粉末。
林心萍找到带队的王政委,提出了下山的想法。
“下山?就现在这天气?”
王政委的眉头拧成了疙瘩,看向窗外依然白茫茫的一片,
“小林,这不是闹着玩的。山路本来就险,加上这积雪,太危险了。”
“政委,我必须去一趟。”
林心萍拿出那本郑卫国的日记,翻到有关阿依夏木的几页,
“日记的主人,还有哨所里很多老兵,心里都牵挂着这个藏族小姑娘。我想找到她,把后来的故事带回来。这不仅仅是找到一个故人,更是连接起一段断了线的军民情谊,是给老虎牙一个温暖的句号。”
她的眼神坚定,语气平和却不容置疑。
王政委看着这个外表文静,内心却有一股执拗劲儿的女作家,又看了看她身旁已经默默开始检查行装的戚何,知道拦不住。
“要去可以,必须有人跟着,还得是最熟悉山路的人。”
王政委最终松了口。
“我去!”
陈大勇立刻站出来,
“扎西村我熟,卓玛阿妈家我也认得路。而且这天气,我更知道哪儿能走,哪儿不能走。”
最后,一个三人小队组成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