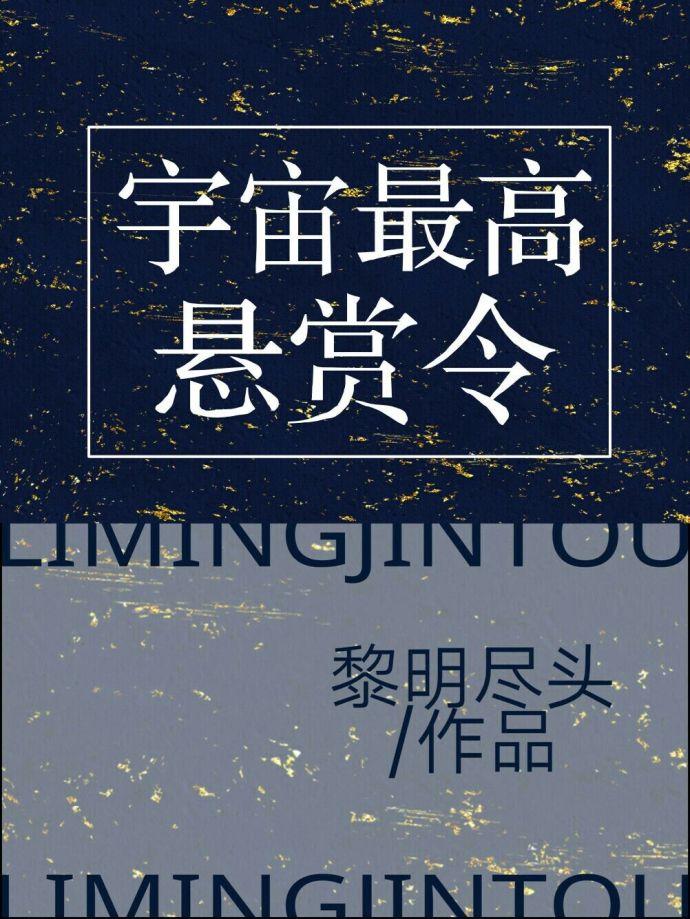无线文学>闻君有两意 > 6070(第4页)
6070(第4页)
那年他不过是风寒发热,可她却心疼得眼睛发红,整整一日就守在他的榻边,一边煮着热茶,一边轻声哼着不知从何处学来的江南小调,唱得倒是像模像样,尾音微微上扬,带着几分生涩的婉转。
他烧得糊涂,朦胧中依稀记得那唱词,大抵是“茅檐低处,溪上青草,遥望谁家炊烟早……”
也是在洮州,也是在这时节。屋外风雪漫天,屋内小火炉上的茶吊子咕噜咕噜冒着热气,茶水滚了又滚,她不厌其烦地吹温,又柔声哄他再多喝一盏。
稍一回想从前和如今的差别,方才咳痛的喉咙里像是吞了一块热炭,既刺烫,又涩苦。
凝滞片刻,他掀开锦被躺了回去,长臂一探,直接将人捞进了怀里。
折柔毫无防备,后背骤然地撞上一片温凉坚硬的胸膛,青年峥凸的锁骨如刀锋般抵在她肩胛上,硌得她隐隐作痛。
她不自觉地绷紧了身子,一瞬间连呼吸都屏住了。
陆谌一只手臂揽住她的腰肢,埋头在她颈间嗅了嗅,像是野兽在逡巡自己的猎物,“装睡,嗯?”
折柔抿了抿唇,依旧背对着他,一动不动。
陆谌眸光沉了沉。
她只肯用后背对着他,乌浓的长发散乱,遮住小半张脸颊,让他丝毫瞧不见正脸神情。还是这副脾性,心中不满便缩在被子里,抿着唇不理人。
冬被厚重,这般拢盖在身上,越发显得她身形单薄纤瘦,半边肩膀还不及他一只手长,偏生处处都透着股倔劲。
陆谌干脆使了些力道,强硬地将人扳过来,掐起她柔软的脸颊,带着几分惩戒的意味,低头狠狠吻了下去。
折柔愣了愣,将要挣扎,便被他一手牢牢制住,压得愈紧。
温热湿润的呼吸不由分说地侵入进来,裹挟着茶水的清苦涩意,又隐约混杂了一丝血气。
这个吻来势汹汹,陆谌用力抵开她的齿关,勾起她的舌尖咂弄纠缠,不容半分抗拒,仿佛要将她的呼吸吞吃殆尽。
舌根被吮得发麻,折柔渐渐地有些喘不过气,呜咽着想要挣脱,却被他更用力地扣住后脑,硬是渡了口气给她,迫着她和他津液交缠,呼吸间都是他的气息,再也分不出彼此。
直到察觉到怀里的人慢慢放软了身子,喉咙里的呜咽化作喘息的轻哼,他的动作才跟着温柔下来,轻啄慢吻,掌心揽住她细软的腰肢,把人往怀里带了带,将她搂贴得更紧。
手上也作乱,带着薄茧的指腹细细抚过她后心一节一节的脊骨,折柔教他惹得一阵阵轻颤起来,忍不住微微向后仰起脖颈。
陆谌呼吸渐沉,唇舌下移辗转,在那截白嫩的纤颈上吮咬出星点红痕,似乎唯有如此真真切切地留下自己的印记,方能教他稍觉满足。
停顿片刻,他哑声开了口,温热的薄唇仍贴在她颈间,说话时带起微微的震颤,“那夜在船上遇刺后,肺腑余毒未清,到如今一直不好过。有劳宁大夫明日给我看看,开两副方子,成么?”
折柔总算匀顺了呼吸,自然不肯应允,淡淡地偏过脸去,“翰林医官局各个都是杏林妙手,比我高明太多。”
陆谌低笑一声,吻了吻她的耳垂,沉哑的声音裹着热息,暖着她的耳,“那群庸医,如何比得过妱妱圣手。”
“更何况,”他用掌心轻轻摩挲着她的脸颊,语气却不容置疑,每个字都咬得极重:“妱妱,这是你欠我的,合该你来还。”
这话说完,折柔怔了怔,半晌没有应声。
陆谌一顿,抬头去找她的眼睛,却见她揪紧了被衾,肩头微微发颤,似在竭力压抑着什么。
等了许久,她终于开口,声音轻得几乎教人听不见。
“那你欠我的呢陆秉言?”
陆谌不由一怔。
折柔抬眸看向他,喉头发涩,眼中渐渐泛起雾气。
陆谌是很细心,很体贴,也疼惜她,照顾她,可他却也一直在强求她,逼迫她。
他给的,她不得不收,他想要的,她也不得不给。
他这个人,性子太过偏执,爱恨都极致,爱之欲其生,恶之欲其死。
他若想做些什么,她没有分毫反抗的余地,这如何不教她害怕?
他越是强求,她便越是害怕。
害怕被他打磨得一点点失去自己,却又无力挣脱,只能忍耐、承受、变得麻木。
更怨恨他对她说那些难听话,做那些难堪事。
折柔不自觉地攥紧了被角,声音很轻,“陆秉言,在燕子坞的那几个月,没有人强迫我,也没有人欺侮我,我凭自己的本事过活,平素虽过得清苦些,却很自在,很安心,也很欢喜。”
“可你却非要强逼我回来,按着我低头,我不喜欢过这样的日子,也不想过这样的日子……”
她越说越痛,却又无比清楚自己说什么都没有用,忍不住微微蜷缩起身子,隐有哽咽,“你既有权也有势,正当好年华,日后前程一片大好,上京城中多得是女子愿意嫁与你……何必非要强求我一个,放我走罢……”
何必非要逼着她,一点点消磨掉她对他的情意,让好好的少年夫妻,走到如今这一步。
“不准。”仿佛被一盆冷水兜头浇下,陆谌心中的戾气陡然翻涌起来,额角青筋突突直跳,黑眸沉沉地望着她,咬牙道:“总之,我不准。往后若是再提半个字,我……”
“你怎样?”
折柔听他这般蛮横,语气里不由带上几分压不住的怨愤,恨恨打断:“如今我人也被你强留下来,你还要怎样?”
陆谌呼吸一滞,定定地看着那双漫起水雾的倔强秀眸,喉结艰难地滚了几滚。
他还要怎样?
人是留在了他身边,可越是这般触手可及,便越是叫人不甘,越是叫人想索要更多。
要你爱我。
要你如从前一般爱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