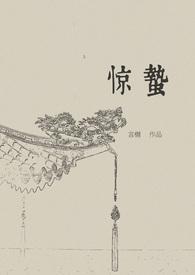无线文学>给星穹铁道来点死亡震撼 > 第401章 惊变(第4页)
第401章 惊变(第4页)
第一站,旧璃月层岩巨渊边缘,某处已被私人武装控制的非法黑矿场。
这里早已脱离了总务司的管辖,成为法外之地。
矿洞入口被粗大的铁栅栏封锁,其内昏暗潮湿,挤满了如同牲口般被铁链锁住脖颈、衣衫褴褛、骨瘦如柴的矿工。
琴下令解除镣铐,分食物和伤药。
“陛下有令,会惩治这些奴役你们的恶徒,帝国会安置你们,给予土地和补偿……”
“你们自由了!”
然而,预想的喜悦却没有生——
矿工们依旧沉默。
其中一位老者仰头,目光越过她,望向更远的皇城,声音沙哑的不成样:
“……皇帝……就是天底下……最大的主子……”
“要杀……先杀他……”
声音很轻,却被一阵恰好卷过的风,清晰地送到了琴的耳边,也送到了每一个靠近的执法队员耳中。
风沙扑面,拍在琴的面颊,生疼。
……
第二站,帝国某行省税署衙门后院。
封条张贴。
抄没的财物堆积如山。
税署主官及其核心党羽已被羁押,等待审判。
然而,就在执法队清点财物时,一个抱着婴儿的年轻妇人,连滚爬爬地冲过警戒线,扑倒在琴的军靴前,死死抱住她的腿。
“琴将军!琴大人!求求您!开恩啊!”
妇人仰起满是泪痕的脸,声音颤抖:
“我夫君……我夫君他只是个管账的!他什么都不知道!都是上面的大人逼他做的!账目都是他们做好的,他只是……只是照着录入而已啊!”
“他知道错了!真的知道错了!”
“求您看在孩子还这么小的份上……饶他一命吧!”
“他若死了……我……我和这没爹的孩儿……往后……可怎么活得下去啊!呜呜呜……”
怀中的婴儿仿佛感知到母亲的绝望,张开嘴,出撕心裂肺的、一声接一声的啼哭。
那哭声并不响亮,却像钝锯割着琴的耳膜。
……
第三站,旧蒙德城郊,一处私人“丝庄”兼高级妓馆。
绣楼之内,暖香袭人,脂粉气与甜腻的酒气混杂在一起。
被解救出来的女奴们聚集在大厅,眼神惊恐不安。
可当执法队员试图将涉嫌逼良为娼、虐待奴役的“庄主”及其打手带走时,出乎意料的一幕生了。
好几个女奴竟然扑上前,拦在了那些满脸横肉的打手身前,对着琴和执法队哭喊哀求:
“军爷!求求你们,别抓走主人!”
“主人对我们很好……给我们吃穿,教我们技艺……离开了这里,我们还能去哪里?”
“我们无家可归了……只有主人收留我们……”
“请不要伤害我们的主人……求求你们了……”
她们跪在地上,磕头如捣蒜,鬓散乱,裸露的肌肤上清晰可见新旧交叠的鞭痕、掐痕与其他施虐留下的印记。
她们颈间的金铃叮当作响,曾是锁链,如今却成了“家”的印记。
……
一月之间,琴率领执法队踏遍七国故地,剑未真正出鞘饮血,心却已千疮百孔。
她见识了底层在长期压迫下滋生出的扭曲。
她面对了罪恶链条上,依附者基于生存本能的哀告和道德绑架。
她更遭遇了被彻底驯化、将施暴者视为唯一依靠、甚至主动维护罪恶体系的受害者。
每一幕,都在冲击着她心中那非黑即白的正义观念,都在拷问着“除恶务尽”背后,复杂的人性。
她不敢回宫复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