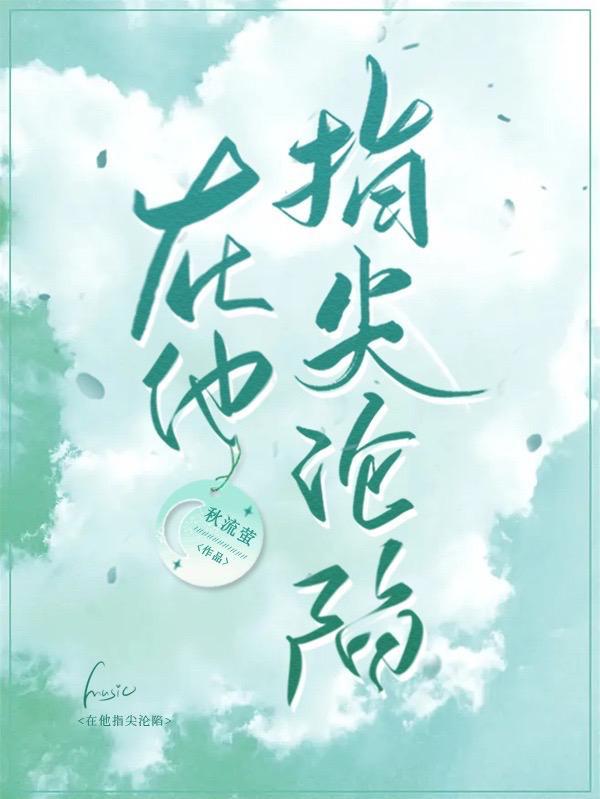无线文学>念旧 > 第223章(第1页)
第223章(第1页)
汤雨繁侧躺着,右耳压在湿漉漉的发尾,隐隐发热,动脉跳动,让她以为听到了心脏的声音。
这两天过得比一礼拜都充实,却没觉得累。
累和疲惫还不同。累是你撑着还能去洗个热水澡,换件干净睡衣抱着西瓜看电视,直到看睡着,歇一晚上就过来劲儿了。疲惫是六月底的梅雨天,让你不想动弹,不想睁眼,从头到脚的黏热用水冲不掉,只想一觉睡死在雨里拉倒了。
汤雨繁没敢闭眼,一闭眼,各路牛鬼蛇神又要往她脑子里蹦,一会儿是葛霄左眼包成木乃伊,蔫头巴脑说你别生我气,一会儿是葛鹏程死死掐着他的脖颈,手臂反折,狠狠往下捣,一会儿是她坐在葛霄车后座,拿他手机听英语,葛霄一说话就震得她脑门发痒,他说,我生日你要不要来?
汤雨繁翻了个身,动静有些大,惹得方才还在倒吸凉气的两位顿时噤声。
“汤啊,吵到你了吗?”张子希颤颤巍巍地问。
“没有。”汤雨繁说,咬字含糊。
张子希错愕地看向邓满,口型:哭了?
邓满摇头示意她别管,摁了空格键,继续播放,顺手调高了声音。
满打满算分开三个月了,从前虽说有些消沉,但到底没因此放肆地宣泄过眼泪,是憋着不哭还是根本不想哭,她自己也搞不明白。
汤雨繁太执着于给这段关系研究出个结论来——分手,还是没分手。
一来是想给自己的消沉找个发泄之处,二来,说白了是她不想承认他们分开了。
不认,不甘心,连一个正儿八经的告白都没有就直接快进到分手了,这算什么。
想到这儿,汤雨繁又有点儿想笑,好蠢。
她合上眼,枕头套上都是眼泪水,枕得半边脸都湿漉漉的,慢慢蜷缩,虾子似的弓着腰,缩起来。
为什么……违心话总最容易说。
她和老妈吵架情绪都没如此外放过,真是昏了头,气他,也气自己。当时哭一鼻子,这会儿又哭一鼻子,仿佛斗嘴欺负他的人不是她,这会儿心疼他的人也不是她。
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睡了过去,半晌睡半晌醒,第二天起床脑瓜疼得要开裂,昨天睡前没擦干头发。
汤雨繁头昏脑胀地爬下床,一看手机才六点多,另外两位室友均在梦乡,她简单收拾了课本,出门。
周一她和张子希有早八,邓满没有,但她每天七点都要爬起来晨跑。
今天醒得晚了些,邓满迷糊一会儿,想起来张子希今天好像有课,喊她:“希子。”
声音过于虚弱,喊了好几声,对面床的张子希才听到,回应同样虚弱:“干嘛……”
“你周一不是早八吗。”
五秒后,张子希鲤鱼打挺,猛地坐起来:“我靠!几点了?”
“七点四十,”邓满又看了眼手机,更正,“啊,现在四十二了。”
紧接着是一段龙卷风过境般的手忙脚乱,张子希爬下床,边拿牙刷边穿裤子,才想起来问:“汤呢?”
邓满侧趴在枕头上,朝空荡荡的上铺努努嘴:“走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