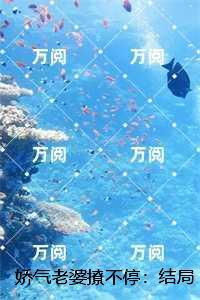无线文学>皆难逃 > 26第二十六章(第2页)
26第二十六章(第2页)
宴安心里本就乱作一团,又被他这般一问,竟一时怔懵到不知所措。
沈修见她默不作声,便以为是在默认,便温下声道:“那往后……我便如此唤你。”
“啊……这……”宴安犹豫着缓缓开口,然还未说出,那在屋中久等不见宴安回来的何氏,有些坐不住了,朝外喊道:“安姐儿?是何人啊?”
宴安忙与祖母回话道:“是沈先生!”
说罢,便先将沈修往屋里请。
何氏见到沈修,就如同见到救星,赶忙将方才隔壁之事与他说了一遍。
说完,她又将心头忧虑道出,“要说两家平日也是极为和睦的,可这出了这档子事,家中只剩我这把老骨头和安姐儿,我这心啊,总觉得七上八下的……”
沈修闻言,眉头紧锁,目光落在宴安脸上,她虽强作审定,可那泛白的面色哄不了人。
沈修心头一紧,当即便开口道:“阿婆放心,这几日我每日早晚皆来一趟,白日进屋说话,夜里……”
从前宴宁尚在家中,身为师长他来宴家也算合乎情理,可如今宴宁不在,他身为外男,夜里若频频来寻,到底有些不成体统。
沈修默了一瞬,抬眼看向宴安,轻道:”夜里我过来,不进院子,只在外面朝里看,若见棚角传出光亮,门闩也是完好,我便知无事,即刻回去。”
何氏眼中含泪,连连应谢,“那可会太过劳烦先生?”
沈修笑着摆手,“沈家就在西南角,与宴家不过百步之遥,算不上麻烦,便当做是饭后消食罢。”
宴安欲言又止,然左思右想,似也只有此法可行。
“那便劳先生费心了。”宴安低声说完,忽又想起一事,“先生今日过来,可是有何要事?”
沈修心道,若无要紧事,便不能寻她么?
然他只是心中想想,面上还是如实回道:“我知宴宁初十赴京,今晨特意从县里赶回来想送他一程,没想还是错过了。”
宴安闻言,眼睫微垂,“宁哥儿走得急,天未亮就上了驴车,便是与先生错过,他心中定也会万分感念的。”
沈修唇角微弯,望她的眸光愈发柔和。
沈修临走前,特意在院子里与宴安说话,那声音故意比平日里扬高几分,说待夜里再送些东西过来。
宴安心知他这是故意说给隔壁听的,便配合着应声。
沈修走后,白日里宴家便未再来人,小院静悄悄的,隔壁也未见再有何异动。
到了夜里,宴安从柜中取出一红色巴掌大的小灯笼,挂在院中那棚角处。
宴安也不知沈修何时会来,只知这院子土墙不高,夜里点了灯笼,他若来时,只稍一抬眼,便能看到光亮。
沈修未曾与旁人说,只道身子不适,叫小厮帮他将后面几日行程全部推了。
他是晌午不到巳时,从宴家离开的,到了午时用过饭后,便说要外出走动,特地拐到宴家门前,未曾叩门,而是静静等了片刻,见里面未有已响,才又回到家中。
未时,沈修再次寻来,同样没有叩门。
申时,酉时,戌时……几乎每过一个时辰,沈修皆会出现在宴家门外。
到了亥时,看到那盏灯笼将院里照出一角光亮,沈修倏然觉得安心不少,然他并未立即离去,而是唇角带着抹温润的弧度,踩着月色,在门前静默等候。
夜里风寒,沈修却并不着急离去,甚至待得比白日来时更久了些。
也不知到底过了多久,四周只剩一片寂静,他才终是提步离开。
宴安今晚注定睡不踏实,她但凡合了眼,眼前便时而是赵伯坐在王婶身上,怒目圆睁地掐着她脖颈发狠的模样……
时而是王婶扑在炕边满脸血泪的哭诉……
时而又是赵伯浑身酒气,不住往她怀里扑的画面……
还有她今日手持菜刀,冲着赵伯呵斥时,那刀柄沾着冷汗的黏腻感,也无比清晰……
宴安猛地睁开了眼,四周一片漆黑,也不知此刻是何时,但听阿婆呼吸沉稳冗长,想来已是到了深夜。
她下意识抬眼去看屋中那布帘,然宴宁不在,布帘并未拉上,那里间空空荡荡,一片幽暗。
宴安头一次这般想念宴宁。
若他在家,她应当不会这般害怕。
宴安正想着宴宁,便听院子里似是传来了一声奇怪的响动。
她心头倏然一紧,呼吸即刻屏住,侧耳细听。
已完结热门小说推荐
- 娇气老婆撩不停:结局+番外乔枝陆擎乔枝陆擎
- 边的车灯忽明忽暗,但男人那张脸轮廓锋利,眉目如炬,那种强烈的压迫感乔枝再熟悉不过。乔枝迫使自己攥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