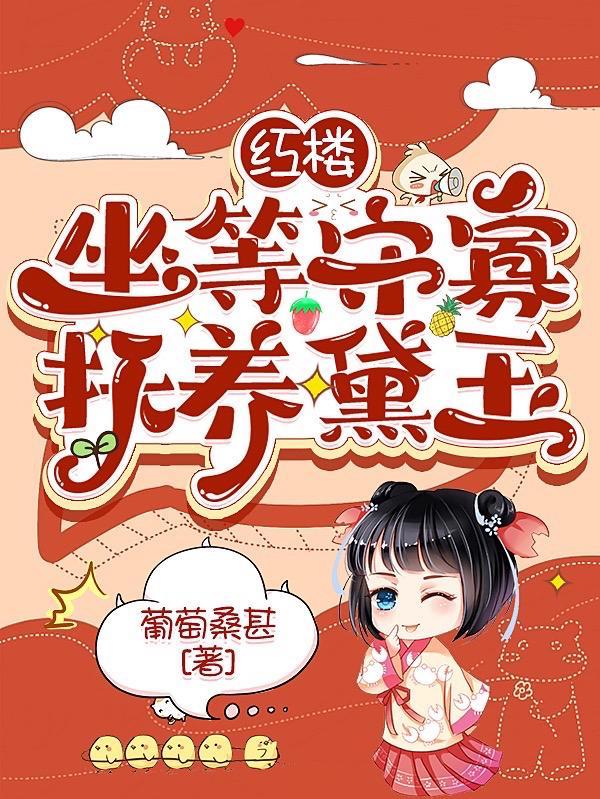无线文学>死对头误食吐真剂后 > 2030(第12页)
2030(第12页)
许知行合着眼,半靠在靠枕上,半梦半醒般说着:
“谢谢你送我玫瑰。”
不知想到什么,许久,许知行又接道:
“我好高兴。”
从机场回市区至少要一个多小时,好在凌晨车少,蒋淮一路开得又快又稳,到许知行家时,已经凌晨三点了。
最快明天七点,蒋淮就要再度出门工作,许知行也清楚这点。
车子一停,许知行就主动说:“你就在这儿过夜吧。”
蒋淮从善如流。
许知行家还是那样,那个魔方也依旧那么突兀。
但蒋淮一进门,就发现了它的不同:
许知行在家里添了个一个不大不小的鱼缸。
他并不了解鱼的种类,因而里头养着几条最常见的草金,体型中等,慢悠悠地游着。
“你养鱼了?”
蒋淮不知该作何反应,走进去看,鱼缸的布置十分专业,称得上很用心。
“我想知道养鱼是什么感觉。”
许知行诚实地答。
蒋淮回过头,看见他难得平和真诚,心里发痒:“是因为我吗?”
“是。”
许知行轻声说。
他越过蒋淮,直直地走向房门。彼时西服外套脱了,露出瘦削的身材,堪堪地挂着件衬衣。蒋淮看见他的背影,甚至有种错觉:
如果是现在的体型差,他可以很轻松地将许知行扛在肩上。
可怎么会这样的?
明明高中时,他们的体型还没什么区别。
倒不如说许知行从小就比他高一些,两人的身高差直到高中时才逆转。
许知行将玫瑰放在桌上,径直走进主卫。
蒋淮隔着远远的门,专注地听里面的水声。
许知行出来时见他立在门外,有些意外,又有些拘谨:“你可以进来的。”
“毕竟是你的卧室,我还是不进去了。”
蒋淮打了个哈欠,熟门熟路地说:“我借用客卫,很快就好。”
说罢,就转身要走。
“蒋淮。”
许知行叫住他。
蒋淮回身,用眼神询问他什么事。许知行沉默两秒,回道:“你就在这里洗吧。”
房间里只开着盏床头灯,昏暗朦胧。这是蒋淮第一次进许知行的卧室,和他在旧家那间二十多年的卧室不同,许知行的卧室宽敞整洁,充满设计感。
不知他用的是什么香薰,一踏入房门,蒋淮就闻见一股令人舒心的香气。
许知行微微让开一些,示意蒋淮走进去。
擦肩而过时他有些恍惚,许知行好像又在主动袒露什么——
主要邀请他进入更私密、更无人探访的角落。
蒋淮注意到那些细节:许知行的床、被褥、香氛;桌上放着的书、浴室里的洗剂、朦朦胧胧的灯——许知行的一切。
一切都暴露在蒋淮眼前,犹如平缓湖面下暗潮汹涌的涟漪。
这种袒露好像是一种示好,又像是种献祭。
他不明白许知行是不是将自己献祭给“爱”,情愿成为“爱”的奴隶。
关于许知行的谜题,蒋淮永远猜不透。如果答案是“是”,蒋淮无法不为他的勇气鼓掌。
本就疲惫的大脑一遇上热水,更是凝结得无法思考。蒋淮洗了个糊涂澡,出来时,只见许知行坐在床边,就着床头精致的小灯端详那支玫瑰。
听见脚步声,许知行没有抬头,只是缓缓地说:
“你知道我看见它时,脑海中在想什么么?”
“什么?”
“幸好——”许知行顿了一下:“幸好我今天戴了镜片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