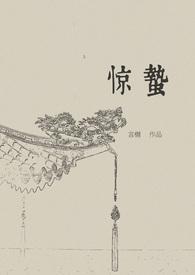无线文学>全汴京在等我的外卖 > 7080(第12页)
7080(第12页)
葛明和沈芙蕖是有一段渊源的,他是通州人,家有七十老母,三岁小儿,从前和沈芙蕖同住在草市坊一条街。
住在草市坊的人,生活都拮据,但葛明比其他人更穷些,穷到揭不开锅。
那时候,沈芙蕖刚支了小摊,几个同样贫困的秀才一起想了个主意,每人凑一点钱让沈芙蕖送餐吃,也算是间接接济了葛明。
但他们也没钱,一天花不到一个铜板,沈芙蕖常常还要自己贴钱。
其实当时沈芙蕖连自己也不太能顾上,但是瞧见葛明苦读的样子,总是于心不忍。
葛明是囊中羞涩到连一个胡饼都要掂量再三的人,更别提购置灯油。入夜后,他只能借着邻家透出的微弱光亮,或是蹲在酒楼脚店门外,就着那点光看书。
书,是断然买不起的,只能厚着脸皮向同窗或书铺恳求借阅,并承诺限期归还。于是,抄书便成了他每日必备的功课。
汴京的冬天,寒风如刀,呵气成霜,墨盒常被冻住,他需将它捂在怀中,用体温将它一点点化开。
冻疮叠着冻疮,裂开深深的血口,每翻一页书,每写一个字,都钻心地疼。鲜血有时会不小心染在借来的书页上,他只得惶恐又仔细地擦拭干净。
夜里,葛明常常被冻醒,只得起身在狭小的屋内来回跑动,待身体回暖,再继续攻读。
那时卖炊饼的张大娘总是讥讽沈芙蕖,自己都顾不上了,还贴钱养着这些穷酸秀才。
读书人,要面子,自尊心强,见有人这般嘲讽,就不好意思再找沈芙蕖送餐。
沈芙蕖便想了个办法,让他们以劳代饭,比如自己告兄嫂的诉状便是找葛明润色的,她付一些润笔钱。开启小食预定后,也经常找他们跑腿,不付钱,只管饭。
等到沈芙蕖开了食肆,每逢新品试吃,也都想着他们。
那几个读书人饥一餐饱一顿,但总算把书继续读下去了。
寒窗苦读多年,如今终于有了回报。沈芙蕖听到葛明中了进士,自然也替他高兴。
“沈姐姐!葛秀才……不,葛进士会当大官吗?”程虞也很高兴,她觉得自己和大官有了交情,是件很自豪的事情。
沈芙蕖想了想回答道:“三甲进士,很厉害了,起码是个县令呢……有人要订两桌酒席,我得去确认一下菜品,你们聊……”
距离午时还有一会,伙计们便聚在一起闲聊。
“万般皆下品,惟有读书高……葛进士以后可是再也不用挨冻了!以后就是衣锦还乡了!”张澈羡慕道。
大双随口道:“要我说,兄弟你这般机灵脑子,干脆也去考个功名试试!”
张澈若要读书,得回宋州原籍,由当地官员考核,才能作为贡生资格方能回到京城参加考试。
备考科举是全天候的任务,需要常年累月地读书作文,若是离开芙蓉盏,张澈就没了生计,谁来供他读书呢?
张澈道:“葛进士再怎么说也有个秀才的爹,七八岁开了蒙,四书五经滚瓜烂熟,我这半路出家的,乘马车也追不上人家。将来……将来,一定让我儿读书就是!便是砸锅卖铁,也要供他堂堂正正地念圣贤书!”
张澈这话,是说给他自己听的,程虞听了悄悄红了脸,“阿澈现在这样也很好呀。”
“怎么,阿虞,你不想当个进士娘子?你想想,你若是当了进士娘子,出门就是大轿子,人人尊称你一句夫人,从此以后绮罗绸缎随便你穿,威不威风?!”小双道。
程虞捧着脸道:“好威风呀!那以后人家就不会看不起我是个厨娘了……”
大双嘀咕:“你说,咱们是挣了点小钱,可始终被视为杂类。胡员外不就是个现成的例子,别看他捐了个官,这汴京城可没一个瞧得上他的。如今女儿的事情一闹,更无人替他说话,我听说,他都打算辞官回鄂州了。”
“阿虞!咱们醉蟹还有多少啊,够不够上两盘的?”这时,沈芙蕖急急忙忙从后厨走了出来。
几个伙计看见沈芙蕖走过来了,都不再说话。
回想那天,马车停在芙蓉盏门口,车帘一掀,大理寺的陆大人先从车上跳下来,随后,沈芙蕖竟搭着他的胳膊从车里一跃而下。她打扮得漂漂亮亮,怀抱一束荷花,满脸是藏不住的喜气。
两人的往来显然超越了正常的范畴。
你说他们的沈掌柜好吗?
当然极好!容貌才情样样拔尖,是女人堆里难得的豪杰,可惜错投了商贾的肚子,哪怕生在寻常耕读之家,也好过如今这般尴尬境地。
两人私下往来,若被御史台的瞧见,弹劾陆却唯利是图、玷辱官箴、勾结商贾,他这官还要不要做了?
唉——可惜啊!几个伙计都这么想着。
不知是谁先喊了声“看榜的相公们来了”,整个酒楼顿时骚动起来,原来是那些高中的士子,一颗心总算落了地,随即便张罗着来到芙蓉盏用午膳。
“恭喜高升!”
“诸位相公这边请——”
“相公要包间吗?”
“坐大堂就可以了!”
“得嘞!”
跑堂的嗓音都比平日亮了,刚撤下邻桌的碗碟,一转身就被个满面红光的年轻士子塞了把铜钱:“拣你们最好的酒菜上!今日某请同窗们吃酒!”
跑堂的忍不住多瞧了他两眼,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,这些相公们,都好气派啊。
一下店里来了这许多客人,程虞等人不敢怠慢,立刻都回到后厨,各司其职。
临窗的座位最抢手,因为高谈阔论起来,颇有些指点江山的感觉,而且既能吸引大家的注意,又不显得太张扬。
几个士子挤在窗前,还在激动地比划着:“方才看见没有?陈兄的名字就在二甲第十七!”
“王贤弟更是了得,竟挤进了一甲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