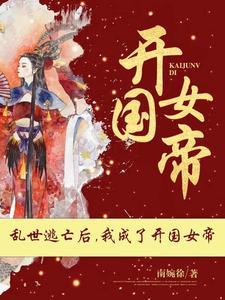无线文学>四合院:十三岁的我被大领导召见 > 第845章 外出务工日常1(第1页)
第845章 外出务工日常1(第1页)
老妇人转过头,眼里带着好奇:“我听说中国的艺术总藏着‘话外音’,就像你们的诗歌,对吗?”
“确实,”顾从卿笑了笑,“比如这剪纸里的鱼,不只是鱼,‘余’和‘鱼’同音,是希望日子能有富余。
就像您看画时会琢磨笔触背后的情绪,我们的民间艺术,也总把心愿藏在图案里。”
老妇人听完,忽然压低声音:“说起来,上周有位议员朋友跟我抱怨,说想办个中国戏曲展,却被人暗中阻挠,好像有人不希望民间交流太频繁……”
她说着,瞥了眼不远处正在应酬的英国官员,轻轻摇了摇头。
顾从卿心里一动,面上却不动声色,继续指着另一幅皮影:“您看这皮影的关节,能活动,就像咱们的交流,得有来有往才能活起来。
不过确实,有时候齿轮会卡住,得慢慢调试才行。”
他刻意加重了“调试”两个字,老妇人会心一笑,没再往下说,只是递给他一张名片:“下次如果有剪纸展,或许我们可以合作。”
送走客人后,顾从卿把刚才的对话记在笔记本上,折了个角。
这种零碎的信息,单独看或许没什么,攒得多了,说不定就能拼出些线索。
他知道自己的位置,不能主动去探听什么,但既然机会送到眼前,多留个心眼总没错。
后来又有几次接待,他都遇到类似的情况。
一次陪英国商会代表吃饭,对方喝多了,拍着他的肩膀说:“你们使馆新来的那个参赞,看着温和,其实非常强势啊……”
另一次整理资料,无意间看到一份被退回的合作提案,上面用红笔写着“暂缓”,旁边却有人用铅笔标注了个隐晦的公司名字——正是上次老妇人提到的那位议员关联的企业。
顾从卿把这些信息像拼积木一样记在心里,从不声张。
他依旧每天准时上下班,翻译时字斟句酌,接待时笑容得体,没人看出他藏在温和外表下的细致。
只有在夜深人静时,他才会翻开笔记本,对着那些零碎的线索出神。
他知道,自己就像棋盘上的一颗小卒,走得慢,却能靠近对方的腹地。
而那些看似无意的闲聊,或许正是解开某些症结的钥匙——当然,这一切都要等合适的时机,急不得。
就像他翻译的那些稿件,总要字斟句酌,才能既准确,又留有余韵。
顾从卿的办公室在使馆侧翼的小楼里,窗外爬满了常春藤,阳光透过叶隙洒进来,在文件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
他每天处理的多是文化交流的函件——比如回复英国某中学关于开设中文兴趣班的咨询,整理下月华人艺术团访英的行程,或是核对民俗展的展品清单,琐碎却不繁重。
下班后,他常换上便装,揣着地图在伦敦的街巷里闲逛。
从特拉法加广场的鸽子群,到泰晤士河边卖唱的艺人,再到胡同般狭窄的老街区里,窗台上摆着的风信子和天竺葵,都成了他观察的对象。
他喜欢去唐人街的老茶馆,听掌柜用带着乡音的英语跟老外讨价还价,看华人老太太坐在竹椅上择菜,说的却是地道的伦敦土话。
有时会遇上使馆的同事,对方笑着问他:“又出来‘采风’?”
他便扬了扬手里的笔记本:“记点素材,说不定下次办活动用得上。”
笔记本里确实记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:某条街道下午三点的阳光角度,街角面包房的肉桂香和胡同里的油条味,哪个更能勾起异乡人的乡愁。
甚至是公园里遛狗的老人说的一句俚语,他也认真标注了对应的中文表达。
这些行走间的发现,偶尔会变成工作里的灵感。
比如他在市集上看到手艺人现场做糖果,便琢磨着下次交流活动可以加个糖画展示。
听到街头艺人用小提琴拉《协奏曲》,就想着或许能促成中英乐手的即兴合作。
他从不刻意去打探什么,只是像海绵一样吸收着这座城市的气息。
有时走累了,就在圣保罗大教堂的台阶上坐下,看鸽子起落,看行人往来。
回到宿舍时,笔记本往往又多了几页字。
经过一段时间细致入微的观察之后,顾从清有了重要的发现。
在伦敦的大街小巷穿梭时,他留意到许多店铺大门紧闭,橱窗上贴着“Closed”的标识,里面的桌椅和货架都已搬空,只留下空荡荡的房间,仿佛在诉说着曾经的繁华不再。
街道上,时不时能看到一些年轻人拿着简历,神色焦虑地在各个招聘点之间奔波,眼神中透露出迷茫与无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