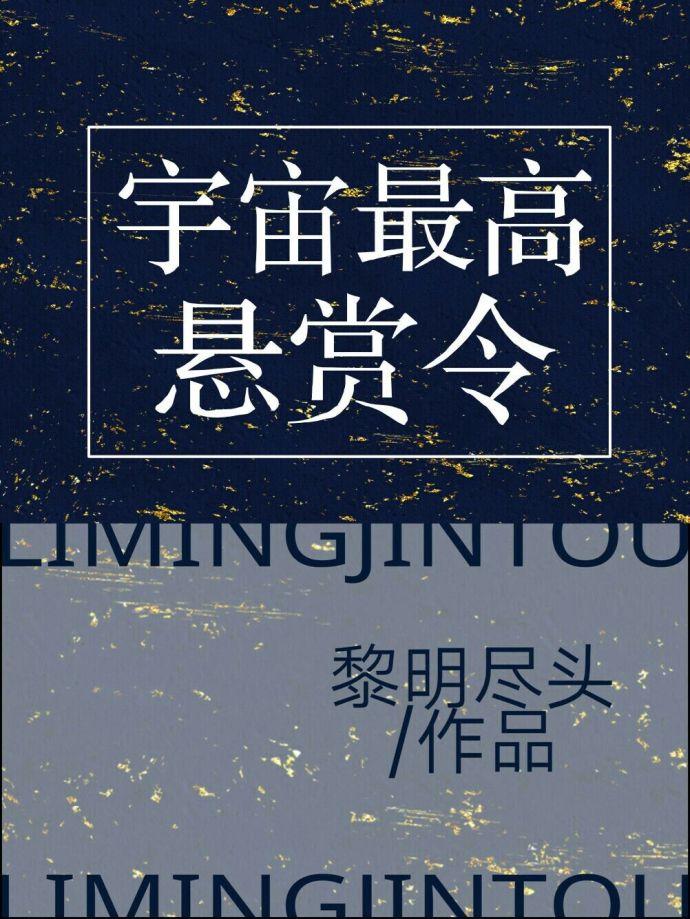无线文学>闻君有两意 > 6070(第2页)
6070(第2页)
见那人转身去了,谢云舟心下微微一松,解开衣袍,安心待刑。
明明周遭冷风凛冽刺骨,可只要一想她曾说过“心悦他”,便觉心头滚热。
虽然他很有自知之明,但她既然说了,那便总是有那么两分的罢。
两分也成。
光是这般想着,欢喜便止不住地从心底漫上来。
他当然要非她不娶。
挨几道鞭子而已,又算得了什么。
这些班直哪个不知小郡王一向最受官家疼爱?就算今日盛怒之下叫人动刑,也是用鞭而非用杖,便是只要他疼,要他吃些苦头,却又不伤及根本。
是以众人下手时都颇有分寸,可刑鞭在朔风中吹得久了,牛皮脆紧发僵,硬如钝刀,不过几鞭下去就见了血,不住顺着他的脊梁蜿蜒淌下。
谢云舟跪在地上,鞭梢剐过皮肉,只觉一阵阵撕心裂肺的灼痛从后背炸开,瞬间蔓延至四肢百骸,寒风裹着雪粒子打在伤口上,更是痛上加痛。
不知捱了多久,喉间血气激荡,他渐渐有些支撑不住,眼前一瞬一瞬地发黑,冷汗混着血水顺着下颌滴落,在雪地上晕开一片触目惊心的红。
五十鞭一到,陈隋当即下令停手,转身匆匆进殿复命。
见他进来,官家声音不自觉地微微绷紧,冷着嗓子问道:“如何,那孽障可知错了?叫他滚进来见朕。”
陈隋垂首盯着靴尖,额上隐隐泛起细汗,喉头滚了滚,“小郡王他……他……”
这般反应,自然已是不言自明。
愣怔片刻,官家怒极反笑,在原地来回走了几圈,最后猛地转身,拂袖一甩,将桌案上的纸墨笔砚尽数扫落,噼里啪啦砸了一地。
“好啊,真是好个硬骨头!”
他喘了几口粗气,又扬声对陈隋厉喝道:“给朕继续打,狠狠地打,这孽障什么时候肯低头认错,什么时候再停!”
不多时,殿外声响又起,怀忠听得浑身发颤,“扑通”一声跪到地上,苦口劝道:“官家……您瞧瞧外头这天儿,又刮风又下雪,小郡王去衣受刑,便是挨得住鞭刑,也挨不住寒气啊,倘若受了风,只怕要落下病根哪……”
官家暴怒的身形一瞬僵住,冷冷地扫了他一眼。
怀忠立时噤了声,俯首贴地,眼观鼻鼻观心,大气不敢再出。
大殿中沉寂得落针可闻。
不知过了多久,官家缓缓地坐回到圈椅中,指尖微抬了抬。
怀忠当即如蒙大赦,麻溜地退出大殿,匆匆跑到阶下,急声喝止:“住手!快住手!”
执刑的班直闻声立即停手,收了鞭子退到一旁,鞭梢却仍在不住地往下滴血,转眼便洇红了一片落雪。
怀忠看得心惊肉跳,快步到谢云舟身前蹲下,仰头看着他的脸,压低声音劝道:“小郡王,官家到底有多心疼您,您心里还不清楚么?就点个头,服个软,应了官家的话吧,成不成?”
额角的青筋突突直跳,谢云舟暗自攥紧了拳,缓缓呼出一口血气,咬牙道:“不、应。”
“诶呦祖宗!”怀忠简直急得团团转,搓着手,声音都打起颤来,“您非和官家较什么劲哪?这血浓于水,打断骨头连着筋,您只要低个头,把这亲事应了,官家疼您都来不及!”
寒风裹着碎雪呼啸而过,谢云舟只觉浑身的血液都在一点点流失,眼前景象忽明忽暗,反应也变得迟钝起来,耳畔的声音像是隔了层罩子,嗡嗡得听不真切。
好半晌,他微微偏过头,舌尖抵住腮帮顶了顶,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,唇角扯出个讥诮的笑:“打死我……也不应。”
不想他竟能桀骜到这个份上,简直是连命都不要了,怀忠一时无法,只能先回殿复命,却不想这一回头,险些和匆匆赶来的官家撞个正着,惊得他慌忙跪地告罪。
官家却看也未看他一眼,目光只死死钉在自家儿子的身上,再走近几步,瞧见他背上鲜血淋漓的鞭痕,玉色袖笼里的指节一瞬捏得发白。
风雪呜咽着卷过回廊,四下里陷入一刹的沉寂。
“抬头!”
雪粒子扑落到睫毛上,谢云舟费力地眯起眼睛,视线有些涣散地看向那双龙纹丝绢软靴。
“朕再问你最后一遍——”
“娶,还是不娶?”
谢云舟喘了一口气,刚要开口,喉间突然涌上腥甜,寒风裹着血沫子灌进喉管,喘息间扯得五脏六腑都跟着抽痛。
喉头艰涩地滚了滚,他硬是将那口血咽了回去,扯唇笑了一下,口中一字一顿,坚定非常:“不……娶!”
“逆子!”
官家气得额头青筋暴起,眼见着他身下积雪都已被鲜血染红,人也冻得唇色青紫,顿觉心头又怒又痛,再也按捺不住,厉声喝道:“逆子!给朕起来!”
僵顿片刻,谢云舟双臂打着颤,勉强撑在冰冷的雪地上,想要借力起身。
可这时节天寒地冻,他在冷雪中跪得太久,双腿早已失去知觉,将将艰难地支起半个身子,便向前栽去。
怀忠见状大惊,急忙要上前搀扶,却听官家一声暴喝:“不准扶!”
怀忠顿时僵在原地,进也不是,退也不是,一时间急得不知要如何是好。
谢云舟咬了咬牙,还欲再起,可强撑半晌,那口气终是没能顶住,整个人重重摔在雪地里,彻底脱力晕了过去。
官家身子狠狠一晃,猛地扬声怒喝:“还不快去请太医!”
四下里顿时乱成一团,诸班直七手八脚地将人背负到偏殿里安置放下。
当值的几位翰林医官闻讯匆匆赶了过来,一边处置伤处,一边吩咐人煎药,金创药的辛辣气息混着血腥味渐渐在殿中弥漫开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