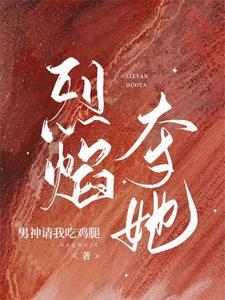无线文学>天人幽冥 > 第155章 赴鹤鸣山大会(第3页)
第155章 赴鹤鸣山大会(第3页)
青鸟几人静静听着,时不时相互对视一眼,眼底满是沉重。这寻常农家的苦楚,字字句句都透着谋生的艰难,让他们更真切地尝到了这世间百姓的不易。
樊铁生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疑惑,向老汉探问道:“这位居士,您家儿子入了那圣灵教,到底在里头做些什么营生?怎么连家里的妻儿老小都不顾了?”
老汉一听这话,眉头瞬间拧得更紧,脸上满是困惑与痛心,声音也沉了几分:“我们也说不清他具体在做啥啊!他从前是最顾家的,对春娃也疼得紧,可自打入了那教,整个人都像变了个模样——我实在想不通,怕不是叫什么脏东西给迷了心窍!”
他顿了顿,像是在回忆当时的情景,语气里添了几分无奈:“前些天他倒回来过一趟,嘴里神神叨叨地念着‘世间就要大变’,还说这次要去益州,要‘干一番大事’。我听着气不打一处来,忍不住数落了他几句,哪成想他二话不说,扭头就走,这都好些天了,再没半点音信……”
青鸟听到“益州”二字,心中一动,立刻联想到龙泉客栈那些疯狂的圣灵教徒,不知那场惨烈的冲突中,是否有这位老翁的儿子参与。想到此处,他不禁为这淳朴的一家人感到一丝隐忧。
正思忖间,娟儿端着一个大托盘走了进来,上面盛着简单的饭菜。春娃见状刚要起身帮忙,娟儿却道:“你去厨房把灶上那盆汤端来。”
春娃脆生生应了一声,小跑着往厨房去。没一会儿,便见他两只小手端着个木托盘,步子迈得稳稳的,小心翼翼地走进来。
转眼间,方桌中央便摆上了热气腾腾的饭菜——一碗粟米混着大米蒸的二米饭,颗粒分明、喷香扑鼻;旁边放着两碟腌菜,还有两盘清炒时蔬,一盘是嫩绿的青菜,一盘是泛黄的豆荚,最中间是一盆飘着香气的菜汤,汤面上浮着几点油花,还能看见切碎的野菜叶,热气裹着鲜气,在屋里慢慢散开。
娟儿用袖子擦了擦额角的细汗,略带歉意地对青鸟几人道:“几位道长,乡下没什么好招待,都是些粗茶淡饭,千万莫要嫌弃。”
一旁的方老汉也热情地招呼:“来来来,几位道长别客气,快坐过来一起吃口热乎的!”
青鸟拱手郑重谢道:“居士言重了。我等清修之人,能得一顿热饭暖身,已是难得的福分,感激不尽。”说着又转向娟儿,“有劳娘子辛苦。”
娟儿连忙摆了摆手,脸上带着爽朗的笑:“道长可别这么客气!快坐,大伙趁热吃,菜凉了就不好吃了。”
樊铁生、张问几人闻言,也不再推辞,纷纷将身下的木凳往桌边挪了挪,围坐成一圈,准备用餐。
众人围坐桌前,开始用晚饭。饭菜虽简单,但在这山野寒夜中显得格外温暖。
青鸟看向坐在对面的娟儿,放缓声音问道:“娘子在客栈做工时,可曾见过身穿玄色道袍,且胸口处绣有这般云纹的人?”说着,他指尖蘸了茶水,在木桌上清晰地画出一个独特的符号。
娟儿探身细看,立刻点头:“见过的!这不就是那个像‘悟’字纹样的玄色道袍嘛。”
一旁的方老汉听得纳闷,转头看向孙女,满脸疑惑地问:“娟儿,你啥时候学会识字了?还能认出‘悟’字来?”
娟儿忍不住笑了,摆了摆手解释道:“我哪会识字呀!这是客栈的沈账房说的,他那天瞧见了,说那些道士衣裳上的云纹,看着就像个‘悟’字。”
方老汉这才恍然大悟,轻轻点了点头:“哦,原来是这么回事。”
青鸟心中忽然一动——他自然清楚那图案实为扶摇派的云纹,并非真是什么“悟”字,但听闻娟儿见过同款道袍,脸上还是忍不住掠过一丝喜色,连忙追问:“娘子是何时见到这些穿玄色道袍的道长的?”
“约莫两日前吧,”娟儿垂眸回忆了片刻,继续说道,“那天都快到亥时了,一下子来了二十多位穿玄色道袍的道长,就在我们客栈住了一宿,第二日天刚亮,便匆匆往鹤鸣山去了。”
青鸟暗自思忖:看来是师父他们途中耽搁了些时日,才会因晚到在客栈歇脚。不过以扶摇派和鹤鸣山道观的渊源,大会期间定然会被安排在观内居住,倒也无需担心。
他正想着,却听娟儿带着几分不满的语气感叹道:“说起来,那些道长大多还算客气,唯独其中一个人,态度格外跋扈——对同门的师弟师妹呼来喝去,一会儿嫌茶水凉了,一会儿嫌房间小了,挑三拣四的。可偏偏对同行的一位长须老道长,又恭恭敬敬的,前后态度差得离谱。这样的人,怎么也配做出家人呢?”
青鸟闻言,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。他心中早已明了,娟儿口中那跋扈之人,恐怕正是掌门师伯座下的大弟子,来高天。
青鸟沉吟片刻,又向娟儿探询道:“娘子可曾留意,有一位四十岁上下、留着短须的道长?另有一位年纪相仿的女冠,带着两名女弟子,虽是同门,但会与那跋扈之人分桌而坐?”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
他心知师父师母门下,除自己与凤锦、凤鸣年岁稍长,其余师弟师妹皆尚年幼,此番必然不会随行。
娟儿蹙眉努力回想,最终还是摇了摇头:“这几日来往的玄门人士实在太多,客栈里忙得脚不点地,依稀有些印象,但具体模样实在记不真切了。”
青鸟闻言,心下释然。想来也是,店家连日应对众多客人,已是疲惫不堪,哪还有余暇细辨每位客人的容貌?他便不再多问,默默低头用完了晚饭。
膳后,王仙君主动帮着娟儿收拾碗筷。几人则与方老汉围坐桌旁,就着粗茶,天南地北地闲话家常。
待王仙君协助娟儿烧好热水,众人简单洗漱完毕,老汉从院中抱来干爽的稻草,厚厚地铺在屋内空地,再覆上一块旧布,便算作临时的床铺。几人就此和衣躺下,在稻草窸窣声中,渐渐沉入梦乡。
次日清晨,天色微亮,娟儿便已起身张罗好了简单的早饭。众人用过饭后,稍做洗漱,娟儿便匆匆赶往镇上的客栈做工去了。方老汉则带着春娃在院子里收拾农具,准备下地。
青鸟见方老汉动作有些迟缓,便想上前帮忙,却被老汉摆手婉拒了。老汉望着手中磨损的锄柄,叹了口气:“家里就这几亩薄田,收成虽不多,好歹是祖上留下来的,勉强够一家人糊口。”
他抬手指向院外连绵的田地,“你们看这鹤鸣庄四周的良田,十有八九都是鹤鸣山道观的地产。”
他顿了顿,语气里带着一丝庆幸:“说来,这道观还算有良心,只收三成租子,剩下的七成归种地的人。别处好些给寺庙种地的佃户,那些和尚满口阿弥陀佛,收租却狠,竟要抽六成!虽说种这些庙产不用向朝廷缴税,可剩下四成粮食,哪里够一家人吃?只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。”
老汉的叹息声更重了,皱纹深刻的脸上写满无奈:“照这样下去,我家这几亩薄田怕是也守不住了。朝廷赋税一年比一年重,实在扛不住啊……”
他顿了顿,继续道:“过些时日,我打算去观里问问,把这田卖了,也去租观里的地种。好歹能免了税赋,剩下的粮食算计着吃,总还能活命。”
青鸟静立一旁,心中波澜起伏。他望着院外那片属于道观的广阔良田,再想到一路所见百姓困苦,不禁暗叹:天下寺庙道观占据大量田产,却皆免赋税,朝廷国库空虚,治理天下的银钱从何而来?最终还不是要转嫁到仅有薄田的百姓身上!这层层盘剥,何时才是个头?
青鸟见阿翁与春娃要开始忙活田里的事,不便再多打扰,便率众人郑重谢过昨夜的收留之恩,告辞离去。临行前,他趁阿翁不备,悄悄在屋内桌案上留下了一吊铜钱。他深知若当面赠予,这位质朴倔强的老人定然不肯接受,唯有以此略表心意。
五人翻身上马,沿着村道向鹤鸣山方向行去。
青鸟几人悄然策马,沿着鹤鸣庄一侧矮山的小径缓缓向大道靠近。昨夜在山林空地中宿营的玄门众人,此刻也已收拾妥当,背着行囊、提着法器,三三两两地从小径汇入大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