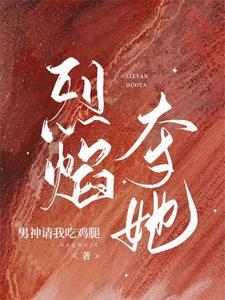无线文学>天人幽冥 > 第155章 赴鹤鸣山大会(第2页)
第155章 赴鹤鸣山大会(第2页)
张问没有立刻应下,而是转头望向另一侧——青鸟几人已翻身下马,正牵着缰绳缓步走近。他目光落在青鸟身上,眼神里带着明显的征询之意,显然是想先听听青鸟的想法。
青鸟上前一步,拱手婉拒:“多谢居士盛情。只是我们人多,恐扰了府上清净。”
“道长太客气了!”老汉连连摆手,脸上露出朴实的笑容,“家里的儿媳和孙女都去了镇上,现下就我和这小孙子两人,冷清得很,谈不上打扰。”
他抬手指向村庄边缘一处隐约的地方,接着道:“喏,我家就在村子最外边,独门独户,清净得很,几位放心住下便是。”
见青鸟几人仍在犹豫,相互交换着眼神,老汉索性上前一步,热情地做出邀请的手势:“几位道长,天色不早了,赶了一天路定然乏了,就别推辞了,随老汉来吧!”
青鸟见对方诚意拳拳,加之考虑到住处确实难寻,且对方家在村外,应当不会惊扰邻里,便不再推辞,点头应允:“既如此,便叨扰居士了。”
张问见事情定下,立刻上前道:“居士,您这背篓看着沉,我来帮您背吧。”不等老汉推辞,他已伸手利落地将那只装满青草的沉重背篓接了过来。老汉只觉背上一轻,对方度之快让他无从拒绝,只得连声道谢,随后转头对那总角男孩吩咐道:“春娃,走快些,给道长们带路回家。”
春娃乖巧地应了一声,牵着牛加快了脚步。一行人便跟着这一老一少,沿着蜿蜒的村间小路缓缓而行。路上闲谈间,一众人方才知晓,引路的老汉姓方。随后,几人也相继报出了此前早已商议好的假姓名,彼此心照不宣,只作寻常路人相交。
行进间,方老汉不免好奇地问起青鸟等人来自何方道观,青鸟依照事先准备好的说辞,从容应对,自称是云游的“道一门”弟子。
走了片刻,前方夜色里忽然透出一点昏黄的灯火。春娃眼睛一亮,当即惊喜地指着灯火处喊道:“阿翁!快看,定是阿娘和阿姐回来了!”
方老汉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,也有些意外,喃喃道:“怎的这么快就忙完了?先前不是说,这几日客栈里客人多,要耽搁些时候么?”
月色清辉下,一行人伴着牛铃叮当声,向着远处那点温暖的灯火走去。
几人随着方老汉和春娃,绕过一片在夜风中沙沙作响的竹林,眼前豁然开朗,一座被林木环抱的农舍出现在眼前。
走近了才现,农舍的院墙竟是由成排的竹子紧密扎成,因墙上爬满了茂密的爬山虎,加之月光被树木遮挡,远看竟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,难以分辨。
几人正将马匹拴在院门口那两棵老槐树上,屋里忽然传来一道清脆的女子声音,带着几分雀跃的试探:“阿翁,春娃,是你们回来了吗?”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
“娟儿,是我们!”方老汉立刻应道,随即抬手朝青鸟几人示意,引着他们往院门口走。
话音未落,院门“吱呀”一声从里面被拉开,一位约莫十六七岁的女子提着盏小灯笼站在院门内。
她先是瞧见阿翁和春娃,随即看到身后跟着的青鸟等几个陌生男子,尤其是樊铁生、石胜这般魁梧身形,不由得微微一怔,脸上掠过一丝警惕。待目光扫过几人身上的玄色道袍,她的神色才明显放松下来,侧身让开通道,方便春娃牵着牛进去。
“阿姐,阿娘也回来了吗?”春娃一边往里走一边问。
娟儿还未答话,后面的阿翁已接过话头:“娟儿,你一个人先回来了?”
娟儿这才回道:“阿翁,今日镇上几家客栈都住满了远道来的客人,忙得脚不沾地,掌柜的央求阿娘留在店里帮忙,明日才能回来。”
她转身从屋里端出一盆清水,轻轻放在院角的石凳旁,才开口道:“阿娘说你们外出回来的晚,让我回来给你们做晚饭呢。”
这时,张问已将背上的竹篓小心取下,阿翁连忙伸手接过,嘴里不住地说着“多谢多谢”,随后快步将背篓放到院角的柴垛旁。转身时,他笑着对娟儿介绍道:“这几位道长是来参加鹤鸣山大会的,夜里寻不着住处,我便请他们来家里将就一宿,添双碗筷的事。”
青鸟几人闻言,当即齐齐向娟儿拱手行礼。青鸟语气温和,带着几分歉意道:“深夜贸然打扰,多有叨扰,实在过意不去。”
娟儿连忙侧身避开,还了一礼,语气爽利又热情:“道长们可别这么说!这几日赶去大会的客人多,镇上的客栈老早就住满了。寒舍虽简陋,几位若不嫌弃,就在这儿歇脚——总好过在野外风餐露宿。”
青鸟闻言,诚恳地回道:“娘子言重了。能得您家片瓦遮头、暂避夜寒,我等已是感激不尽,哪里还会嫌弃。”
娟儿引着青鸟几人进屋,招呼他们在堂屋的木凳上坐下,她转身从桌上取了粗瓷茶壶,给几人一一斟上热茶,笑着说道:“几位道长先喝口茶暖暖身子,晚饭很快就好,你们且在屋里稍坐片刻。”说罢,便转身快步去了厨房张罗晚饭。
青鸟端着茶杯,指尖触到温热的杯壁,目光也缓缓打量起这间屋子。屋子不算宽敞,却处处透着规整干净。
最惹眼的是堂屋正中的桌子,上面摆着好几件瓷器——其中一个白釉瓷瓶尤为亮眼,瓶身上用青料细细绘了几丛兰草,笔触清雅,透着股脱俗的意趣,瓶中还插着几支不知名的野花,花瓣沾着淡淡的水汽,看着鲜润得很,想来是近两日刚采回来的。
再看瓷瓶旁的茶壶,竟和自己手中的茶杯样式、釉色都一模一样,显然是成套的物件,在寻常农家屋里,倒算是少见的雅致。
青鸟正暗自打量,方老汉已安置好牛和草料,掀帘进屋。见青鸟目光落在瓷器上,便解释道:“春娃他阿爷以前在县城的瓷窑帮工,时常带些瓷器回来。”言语间带着几分怀念。
青鸟顺势问道:“听阿翁之意,如今已不在窑上做了?”此时春娃也安静地坐到桌子一侧,先给祖父倒了杯茶水,才给自己也倒上。
老汉抿了口茶水,重重叹了口气:“我那儿子给刘掌柜的窑场干了近十五年,去年突然悄悄辞工不干了。后来刘掌柜派人来家里问,我们才晓得,他……他竟是去入了什么‘圣灵教’。”
“圣灵教”三字一出,青鸟几人虽面色不变,目光却瞬间聚焦在方老汉身上。青鸟语气平淡地接话道:“这圣灵教近来确实流传甚广,只是听闻其内里颇为复杂混乱。”
老汉像是终于找到了能倾诉的人,脸上的愁容愈浓重,声音也带着几分沙哑:“道长您也听说过那教门?我活了大半辈子,从没听过这般荒唐的教派!自打春娃他阿爷入了那教,家里就再也没见过他拿回来一个铜板——一家子的吃穿用度,全靠那几亩薄田撑着,哪够糊口啊?还要应付官府的税赋,年年都紧得揭不开锅……”
他越说越无奈,眼眶都有些红:“春娃他阿娘实在看不过日子这么熬下去,才去镇上的客栈寻了份帮工的活计,拼死拼活地干,才勉强能让一家子不饿肚子。“
他抬眼望向厨房的方向,昏黄的灯光正从门缝里透出来,隐约能听见碗筷轻响,眼中满是感叹与欣慰,声音也软了几分:“今年娟儿刚满十六,也跟着她阿娘去客栈搭把手了。虽说那活计累,挣得也不多,可好歹能给家里添点补贴,日子总算能松快些。”
一旁的春娃听到这儿,小脑袋猛地抬起来,稚嫩的脸上满是认真,攥着衣角说道:“阿翁别担心!等我再长大些,也能去帮工挣钱,到时候就不让阿娘阿姐那么辛苦了!”
老汉闻言,脸上总算闪过一丝欣慰,可那笑意没撑片刻,就被更深的忧虑压了下去。他抬手捶了捶自己不利索的腿,重重叹了口气:“唉,都怪我这腿不中用,连自家那几亩田都侍弄不利索,反倒要靠她们娘儿俩儿受累……”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