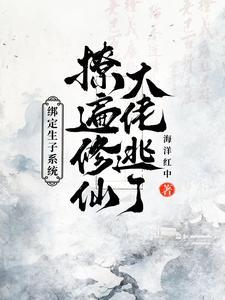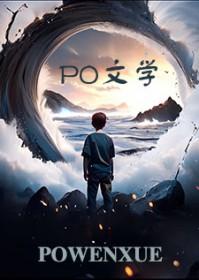无线文学>风水云雷电 > 事情要比想象中难(第1页)
事情要比想象中难(第1页)
周砚冲进站台时,火车正喷着白汽缓缓动起来。他攥着票往前跑,皮鞋底在水泥地上磨出刺耳的响,可车轮转动的度像故意跟他作对,一节节车厢从眼前滑过,快得让他眼晕。
最后他扶着栏杆停下,胸腔里像塞了团烧红的铁,每口呼吸都带着疼。他看着那列绿皮火车越来越远,车窗外掠过的树影晃得他眼睛酸——刚才跑回练功房的二十分钟里,他脑子里全是梁盼娣哭红的眼角,可现在站在空荡荡的站台上,那些勇气忽然就泄了气。
口袋里的手机震了震,是父亲来的消息:“武馆合同已签,你爷爷的老规矩不能破,陈家那边催着定亲了。”
周砚盯着那行字,指节捏得白。他靠在冰凉的栏杆上滑坐下去,背包带勒得肩膀生疼,却抵不过心里那股钝重的闷。他知道梁盼娣在等那个“办法”,可所谓的办法,不过是他跑回来时硬撑的底气。父亲的固执像块磨了几十年的铁,爷爷留下的规矩被供奉在祠堂里,连灰尘都碰不得,而他一个刚毕业的毛头小子,手里攥着的除了半本拳谱,只有满身撞南墙的傻气。
风从站台尽头灌过来,带着铁轨的铁锈味。他摸出烟盒想抽根烟,手指却抖得连打火机都按不燃。练功房里梁盼娣泛红的眼眶又浮上来,她捏着玉佩时指尖白的样子,她强装镇定说“谁哭了”时硬邦邦的声音,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。
他终究还是让她等了。等一个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要耗到什么时候的结果。
烟掉在地上,他抬脚碾灭,喉结滚了滚,却不出任何声音。远处的信号灯闪着红光,像在嘲笑他这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回头。原来最疼的不是赶不上火车的遗憾,是你明明抓住了想珍惜的人,却现自己手里根本没有能护着她的力气。
他掏出那个画着武馆简笔画的小本子,指尖划过自己写下的地址,忽然觉得那几笔线条幼稚得可笑。
周砚终究还是坐上了南下的火车,是下一班慢车,要晃十二个小时才到佛山。车厢里混杂着汗味与泡面味,他靠窗坐着,手肘抵着玻璃,指尖无意识摩挲着裤袋里那枚备用的“缠”字玉佩——原本是想等事情理顺了,亲手给她配成一对,现在倒成了攥在掌心的救命稻草。
车过南岭时,手机又响了,是母亲的声音,带着粤式普通话特有的急切:“阿砚啊,陈家阿妹下午来家里了,给你爷爷的牌位上了香,多懂事的姑娘。你爸在祠堂跟叔伯们说好了,下个月先订亲,年底就办事。”
周砚猛地坐直,玻璃的凉意透过衬衫渗进骨头:“妈,我说过我不答应!那是爷爷辈的口头约定,现在都什么年代了?”
“年代?”母亲的声音陡然拔高,带着哭腔,“你爷爷走的时候怎么跟你说的?‘武馆不能散,香火不能断’!陈家帮我们保住了馆里的地皮,你现在说不答应?你是要让你爸在宗族里抬不起头,还是要把你爷爷的牌位从祠堂请出去?”
电话那头传来父亲的呵斥:“跟他废话什么!他要是敢毁约,就别认我这个爹!”
“啪”的一声,电话被挂断了。周砚捏着手机,指节泛白,屏幕上还停留在母亲那句“你爷爷的牌位”上。他太清楚这句话的分量了。在佛山的宗族里,祠堂是天,祖宗是根,父亲当年为了保住武馆,在祠堂跪了三天三夜,膝盖磨出的血印子,他至今记得。
车窗外的山影连绵起伏,像压在心头的重石。他摸出梁盼娣的照片——是去年拍的,她穿着练功服,手里攥着剑,站在练功房的晨光里,眼睛亮得像淬了火。他指尖划过照片上她的眉眼,忽然想起教她“缠丝劲”时的光景,她总说“师父,我手腕转不对”,他握着她的手慢慢带,能感觉到她掌心的汗,和他自己加的心跳。
“不能让她等成一场空。”他对着照片低声说,声音在嘈杂的车厢里几乎听不见。
到佛山的第二天,周砚直接去了武馆。红漆大门上的铜环磨得亮,门楣上“周馆”两个金字被雨水浸得暗。父亲正带着几个徒弟练拳,见他进来,一记“铁山靠”撞在沙袋上,震得房梁上的灰尘簌簌往下掉:“回来了?先去祠堂给你爷爷上香,然后跟我去陈家赔罪。”
“我不去。”周砚站在院子中央,阳光透过天井落在他身上,却暖不了那股子硬气,“爸,武馆我接,但亲事我不认。”
“你说什么?”父亲的脸瞬间涨红,广东男人骨子里的火爆全涌了上来,手里的长棍“啪”地砸在地上,“你爷爷的规矩!宗族的脸面!你想让周家在佛山抬不起头?”
“规矩是死的,人是活的!”周砚往前一步,胸口起伏,“爷爷教我们练拳,是要我们有骨气,不是让我们拿婚姻当筹码!”
“反了你了!”父亲扬手就要打,却被旁边的大师兄拦住。大师兄是看着周砚长大的,叹了口气:“师父,阿砚刚回来,有话慢慢说。”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
那天下午,周砚被关在祠堂里。供桌上摆着爷爷的牌位,香炉里的三炷香燃得笔直,烟气呛得他眼睛酸。父亲搬来族谱,一页页翻给他看:“你看清楚!光绪年间,你太爷爷跟陈家太公分的地盘,武馆能传到今天,靠的就是‘信’字!你现在说不认就不认,是要让祖宗戳我们脊梁骨!”
周砚盯着族谱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,忽然觉得喘不过气。他知道父亲说的是实话,在佛山这种地方,宗族的纽带比钢筋还牢,一句“背信弃义”,能让周家几代人的名声烂在泥里。可他一闭上眼,就是梁盼娣捏着玉佩时泛红的眼眶,她那句没说完的“等你……”像根丝线,缠得他心口紧。
夜里,他偷偷给梁盼娣打电话,听筒里传来她那边的风声,还有隐约的拳套撞沙袋的声音。“我在练功。”她的声音比平时低,“你……还好吗?”
“我没事。”周砚靠在祠堂的柱子上,声音哑得厉害,“你别担心,好好练拳,等我消息。”
“嗯。”她顿了顿,“我今天练了‘白蛇吐信’,比上次稳多了。”
挂了电话,周砚蹲在地上,肩膀控制不住地抖。他从背包里翻出爷爷留下的拳谱,泛黄的纸页上有爷爷的批注:“缠丝劲,柔中带刚,韧可绕指,硬能破壁。”他忽然想起教梁盼娣练这招时,她总说“师父,我绕不明白”,他握着她的手腕,一点点带她转:“别怕,跟着气走,心稳了,劲就顺了。”
可现在,他的心怎么也稳不下来。
陈家那边很快有了动静。先是武馆的几个老学员被陈家的生意伙伴施压,说要退馆;接着,祠堂门口被人泼了墨,写着“忘恩负义”四个大字;连巷口开了三十年的云吞店,见了他都摆摆手:“阿砚,不是叔不卖给你,是你爸放了话,谁跟你来往,就是跟周家作对。”
周砚开始失眠。整夜整夜地在武馆的院子里练拳,“噼啪”的脚步声惊得邻居投诉。他打“翻拦捶”,拳风扫过空气,却像打在棉花上;他练“十字手”,两手交错时,总想起攥着梁盼娣手腕的温度。有天凌晨,他对着沙袋练“铁山靠”,一下比一下狠,直到肩胛骨传来剧痛,才捂着肩膀滑坐在地上,喉咙里出像困兽一样的呜咽。
他给梁盼娣寄过一封信,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笑脸,说“一切顺利”,却在信封里夹了片佛山的木棉花——那是她上次说想看的花。可他没说,他已经三天没好好吃饭,没说父亲断了他的银行卡,没说陈家阿妹天天来武馆帮忙,明里暗里提醒他“婚约在身”。
最难受的是宗族大会。那天来了三十多个叔伯,围坐在祠堂里,烟卷的烟雾把屋顶都熏黄了。三伯公磕了磕烟斗,慢悠悠地说:“阿砚,男人要懂担当。陈家那边说了,只要你点头,武馆的地皮他们再多让三分,还帮你请省里的教练。”
“我不要。”周砚的声音很轻,却带着股犟劲,“我只要我自己选的人。”
“你选?”二姑丈冷笑一声,“一个北方姑娘,懂我们广东的规矩吗?会拜祖宗吗?将来生了孩子,连粤语都不会说,算什么周家人?”
这话像针一样扎进周砚心里。他确实怕过,怕梁盼娣受不了佛山潮湿的天气,怕她跟宗族里的长辈合不来,怕那些“外乡人”的闲言碎语。可这些怕,在想起她练拳时眼里的光,想起她偷偷哭时倔强的侧脸,忽然就成了笑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