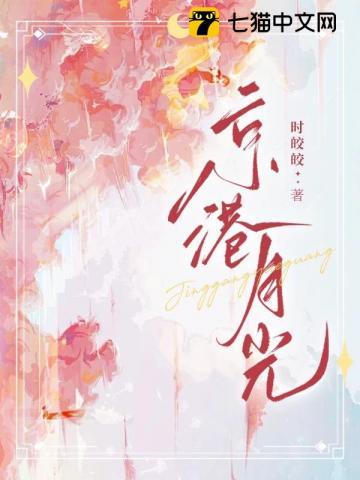无线文学>科举路藏女儿身,终成首辅定乾坤 > 第466章(第2页)
第466章(第2页)
如今,我送她回来。
皇帝的恩旨下来了,说是温淑端慧,慈范永存。
八个字,金灿灿的,刻在墓碑上,很重,很气派。随行的仪仗,护卫,还有同僚们送来的奠仪,排了长长的队伍,从村口一直延伸到我记忆里总是飘着炊烟的老屋前。
村里还活着的老人都来了,站在路两边,拘谨地看着我,看着这他们只在戏文里见过的排场。
但我都不认识,我认识的老人都已经死了。
我穿着粗麻孝服走在灵柩前面。
唢呐声吹得震天响,是京城带来的班子,比沈大人家那次的还要响亮规整。
棺木落入墓穴,黄土撒下去,打在柏木棺盖上,出沉闷的噗声。
阴阳先生拖着长腔唱喏,声音苍老:
“日落西山——兮——,魂归故里——”
“三盘果供——啊——,敬送亡人——”
我捧着那个沉甸甸的孝子盆,按照指引,在灵柩前头用力摔下。
碎片溅开,旁边执事的人立刻高声喊道:“摔盆——起灵——孝子谢恩——”
我跪在冰冷的土地上,对着前来送葬的乡邻,那些陌生又苍老的面孔,深深地叩下头去。
唢呐再次尖锐地响起,吹的是一支我从未听过的调子。
队伍缓缓移动,返回村子。
按照乡里的规矩,每走一段遇到第一个路口,就要停下,摆上几样简单的祭品,一块方肉,三只面果,一盅浊酒。主持仪式的族老颤巍巍地斟满酒,泼洒在尘土里,嘴里念念有词,都是些祈求亡魂安稳,保佑子孙的古老话术。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
路两旁,偶尔能看到几处路祭。那是村里还沾亲带故的人家设的一张小方桌,上面摆着几样奶奶生前爱吃的点心果子。
我作为孝子,每一次都要停下,叩,答谢。
这些规矩,奶奶一定是懂的。
以前村里有老人过了,我们家门口也摆着这种小方桌的。
我俯身叩头,额头抵着冰冷的土地。
起身时,瞥见大丫姐和二丫姐互相搀扶着,哭得几乎站不稳。
可是我已经一滴眼泪都哭不出来了。
我觉得我比她们都冷静,奶奶八十四岁去的,是喜丧。
没关系的。
唢呐再次凄厉地响起,纸钱漫天飞舞。
这七天里,娘和姐姐们像是把眼泪攒成了溪流,总也流不完。
清晨上香时,她们的眼圈是红的,午后听经时,她们的肩头还在微微抽动,就连夜里灵堂那边也偶尔会传来极力压抑细碎的呜咽。
我穿着麻衣,接待前来吊唁的族人乡邻,看着她们时不时抬起袖子拭泪,心里有时会掠过一丝不解。
不是已经哭过了么?奶奶走得并无痛苦,寿数也高,还有什么可一直哭的呢?
我觉得自己比她们都冷静,都明白。
直到下葬后的第三日,我才真正闲下来一些,想着将随身带来的几卷书整理一番。伸手往腰间一摸,却摸了个空。
那块随我多年的羊脂玉佩不见了,那玉不算顶名贵,但雕的是青松祥云,寓意好,我平日处理公务和见客会友都习惯戴着。
我心里一紧,下意识里便在屋子里四处翻找。
书箱里没有,换下的官袍袖袋里没有,床头枕下也没有。越是找不到,心里越是急,那点强撑了许多日的冷静退去,只剩下一种空落落的焦躁。
“我这个”我皱着眉,忍不住脱口而出高声往外面喊道,“奶,我这个玉佩放哪儿了?您看见没有?”
外面一片寂静,没人回复。
我像是突然才想起这件事。
哦,我没有奶奶了。
喜欢科举路藏女儿身,终成辅定乾坤请大家收藏:dududu科举路藏女儿身,终成辅定乾坤小说网更新度全网最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