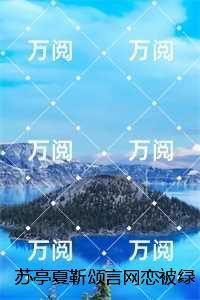无线文学>四合院:你居然给贾家下春药 > 第636章 双方当面谈判(第1页)
第636章 双方当面谈判(第1页)
送走泰国人后,段希文久久不能平静。
傍晚,他站在高地上,看着山谷里。
数个新兵营已经完成了基础训练,正在进行队列操演。
他们穿着缴获的缅军军装,扛着崭新的苏式步枪,步伐整齐,吼声震天。
落日的余晖洒在他们身上,也洒在了那些被擦拭得锃亮的火炮和卡车上。
一支钢铁洪流,正在以不可思议的度成型。
黄智走到他身边,递给他一支烟。
段希文没有接,他看着眼前的景象,声音沙哑地开口:
“指挥官,我打了一辈子仗,从没想过会有今天。”
他的眼神里,有激动,有欣慰,但更多的是一种深沉的敬畏与忧虑。
“我们亲手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。”段希文一字一句地说道,“这支用民族苦难和级大国的利益喂养出来的军队,一旦成型,将让整个东南亚为之颤抖。”
黄智吸了一口烟,吐出的烟雾在晚风中消散。
“颤抖,总比被人踩在脚下要好。”
“这只是第一步,段老。”他的目光望向更远的南方,“有了剑,我们才能谈,家在何方。”
三天后,天空的颜色变了。
巨大的、喷涂着红星的伊尔-运输机,以前所未有的粗暴姿态,在被工兵营连夜拓宽的河谷跑道上降落。
舱门打开,吊装下来的不是坦克,而是电机的涡轮、水泥搅拌机和车床。
随着设备一起走下来的,还有一群金碧眼、神情紧张的苏联工程师。
波波夫大使亲自陪同,他指着这些设备,像一个推销员一样对黄智说:“黄先生,这是莫斯科的诚意。第一批,一个小型火力电站和一座水泥厂的全套设备。后续的,会源源不断。”
黄智点了点头,没有多说,只是对李国辉下令:“成立工业部,让段老兼任部长。把所有会说俄语的人都找出来,配合好我们的苏联朋友。记住,他们的安全和伙食标准,是最高级别。”
苏联人带来的,是奠基的石头。
当天晚上,在刚刚建好的木结构“议事大厅”里,黄智召开了第一次“华人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全体会议”。
到会的,是段希文、李国辉等几十名核心军官。
他们本以为这是一个军事会议,讨论如何扩编部队。
但黄智的第一句话,就让他们愣住了。
“今天,我们不谈打仗,我们谈建国。”
他站到地图前,上面已经不是军事部署图,而是一张行政规划草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