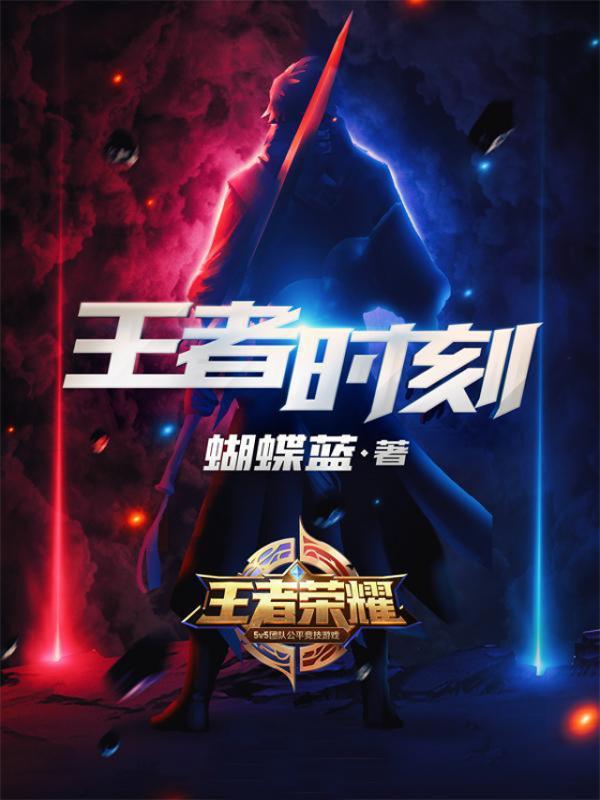无线文学>被争夺的妻子 > 21第 21 章(第2页)
21第 21 章(第2页)
“当然了,还有个帖子,问夫人得空不得空,她想上门拜访。”
一想要和那些贵妇人打交道,南玫就犯怵,喃喃道:“能不能说我没空?”
海棠笑道:“那有什么能不能的,夫人想见就见,不想见连理也不用理,启事处自会回绝。”
“会不会给王爷添麻烦?”
“瞻前顾后,可是用兵的大忌!”门帘一挑,元湛朗朗笑着走到南玫身边坐下,顺势把手伸进她的领口。
屋内婢女们已无声退下。
南玫半推半就,“轻点,疼……”
“几日不见,好像大了些,让我看看,还有哪些地方变了。”
元湛干脆把她抱到膝头,细细把玩,“温润滑腻,最好的羊脂玉也比不过你……嗯?”
南玫脸红了,“身上不大方便,王爷要不找别人?”
“我除了你还有哪个女人?”元湛亲亲南玫脸颊,“以后再说这种话,我打你屁股。”
南玫迟疑片刻,期期艾艾道:“不然……我试试……别处。”
最后两个字比蚊子哼哼还低,幸亏元湛靠得近,才算捕捉到这两个字。
“别处,是哪里?”他的喉结滚动了下,一阵口干。
南玫眼角都羞红了,手指缓缓解开他的腰带。
元湛猛然抱起她滚到床上,狠狠地吮吸她的唇舌,呼呼喘着粗气,“真是叫人爱死你了,这回不成,我马上还要出门,等着,等下次,我非叫你三天起不了床。”
他抱得那样紧,几乎要把她勒死。
紧贴肚皮的阿物挺坚灼人,南玫一动不敢动。
好一会儿,还是消不下去,元湛低低骂了句粗话,把她翻了个身,褪去里衣。
她心惊,却不敢反对。
双腿被紧紧拢住,其间成了另一处缓解宣泄的去处。
他咬牙切齿,气急败坏:“不准再挑逗我。”
南玫同样喘吁吁的,这副身体变得太奇怪了,假做而已,竟也让她生出别样的快慰。
不由暗暗使力。
风突然大了,树影一阵狂乱地摇晃,红的黄的树叶落了一地。
“外面的应酬不去也罢。”舒快后的元湛整理着袖口,“请封王妃的奏本我都写好了,偏生赶上冀州水患,这时候提不合适,只能等明天开春冀州情况稳定了再说。”
南玫根本不想要王妃的封号,闻言忙说:“赈灾可不是到了春天就没事了,起码要两三年才能恢复。”
元湛诧异地停住手,“此话怎讲?”
“其实灾民最难的是青黄不接的时候,秋冬有官府的赈济粮,有大户人家施粥,当官的怕冻死的人太多,面上不好看,冬天也会搭窝棚挡风,只有春天。”
南玫无奈地叹了声,“赈济粮没了,粥棚也拆了,再没人管那些灾民,似乎春天一来,地里就自动长出粮食了。”
“地都被淤泥填实了,怎么种?灾民又哪来的钱买种子?说什么挖野菜采野果捕鱼打兔子,灾荒年,草根都挖没了,蚂蚱都捉来吃了,大地光秃秃的,什么都没有。”
南玫又是一声深深的叹息,抬起头,正对上元湛炯炯的目光。
心忽悠跳了跳,结结巴巴问:“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?”
“没有,你说得很对!”元湛捧起她的脸,亲了又亲,“这些话,我得好好点点那些官儿!”
他走了,南玫摸摸发烫的脸,悬在半空的心终于落到了实处。
没有再提李璋试探她,这一关,算是过了吧。
当时忍住不做那些不要脸的事就好了……
婢女们进来收拾床铺,南玫不自在,便躲到了对面的小花厅。
海棠正在煎茶,忽叹了声,“论煎茶的功夫,绿烟最好,这人啊,在眼前的时候看着她腻歪,看不见了倒有点想她,唉,也是个可怜人。”
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,南玫恍惚了下才问:“她现在在哪儿呢?”
“不知道,没人再见过她,或许死了吧。”
“什么?!”南玫大吃一惊,“为什么?谁干的?”
还能是谁?海棠苦笑:“她太多嘴了,心思不正,落得这下场怨不得别人。”
南玫怔住了,一阵秋风扫过,寒意四起。
-
都城,蓬头垢面的绿烟一瘸一拐走着,看着热气腾腾的小吃摊,不住咽口水。
“走开走开!”摊贩轰苍蝇似地赶她,她跌跌撞撞后退几步,摔倒在路中间。
立时有鞭子落在身上,“死远点,没看我家公子经过!”
绿烟哇哇怪叫着躲避,一眼瞅见高头大马上的人物……有点面熟,再仔细看……是他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