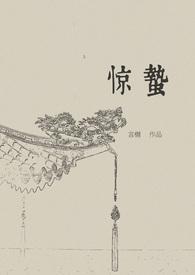无线文学>拉尔曼郡的魔女 > 90100(第16页)
90100(第16页)
他不可置信地睁大眼睛,看自己粗糙的双手,摸了摸跳动的心脏和热乎乎的脖子,他终于确定,他活下来了,在敌人的枪下偷出了一条卑微的性命。
士兵欣喜地抬头望,天上有几朵灰色的云,喜悦的泪水还没从眼眶里落出来,一颗榴弹就掉到了他的腿间。
他怔了怔,忘记闭眼。
两秒后,他的怀里绽放出一朵漂亮的要命的烟花。
……
阿尔米亚一直在战场上奔掠,她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,子弹射入了一个又一个士兵的小腿,她再狠狠地把他们踢下去,踢进两旁的战壕里。
她想对着战壕大吼一声:“他妈的都冷静点!”
但她来不及大吼,她忙着躲避敌人的子弹,忙着从重型炮车密成网的火线里穿梭,她还要抽工夫把跌倒的风车里郡士兵拖回掩体后,看手边有什么东西能替他们包扎一下狰狞的伤口。
在炮火停止的瞬间,她难得的停下来,眺望了一眼远处的硝烟。
“太多了……”
她喃喃道。
白马郡到底有多少人参战,为什么风车里郡的士兵在他们的战防线前这么不堪一击……
奥兰荒原这处籍籍无名的战火线在什么时候隐匿了这么庞大的军队,人数多到一眼望不到边。
象征白马士兵的灰色军团铺天盖地占据了整片荒原,天上所有的乌云加起来也不如他们一个军团庞大。
唐顿·赫曼藏的三十万年轻士兵也从西边涌来,风车里郡原本浩荡的阵势在敌人的对比下却显得渺小非常。
两边的震吼疯狂撞击人的耳膜,没有谁能在这种场面下冷静思考,尤其是指挥官,他们都狂热地观望这处战线,双手作拳狠狠砸在桌子上,每一发沉闷入肉的枪声都在催化他们的欲望。
唐顿拍着桌子站起来,眼里跳跃着火光。
他遥遥望着呐喊最惨烈的战地,听迫击炮和重型炮车碾压发动的声音,阵势之大,令他所在的这处指挥营也在颤抖。
“不能输。”
他不能输,即使三十万风车里郡士兵的尸体覆盖满这片荒漠,他也不能停下来,最惨烈的胜利也是胜利。
第一声吹响号角的人已经不重要,重要的是谁能奏响最后的战歌。
风车里郡必须要通过这场战斗从战争的沼泽里摆脱出来,他们陷在僵局里太久,压在人们身上的枷锁一重又一重,每天睁开眼就要考虑面包,食物,水源,要考虑失去顶梁柱的家庭的未来,要考虑更幼小的孩子的出路。
妻子们目送载着丈夫的列车出发,驶向一望无垠的辉煌的沙漠,她们节省自己的口粮,把衣服缝缝补补又添几针,把一切能在战场用上的东西都细心拿报纸布条包裹,寄到遥远的东南部的前线来。
她们中有些人清楚的知道自己最终只会等来一个简陋的生锈的铭牌,上面刻有她们丈夫的名字,磨损严重的名字,除了这个他几乎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的存在痕迹了。
而另一些人会热忱地等待,等待他们活着回来,她们心中还有一些美好的希望,努力说服自己也说服别人……
再不迅速解决这个局面,他们会被枷锁深深缠进泥泞里,窒息而死。
战争会带给人们什么,是死亡,是痛苦,他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,但他更害怕见到的是看不到未来的绝望。
即使死亡,也要满载荣誉的死亡,每一位牺牲的士兵都将长眠沙丘,庇护这片辉煌又孤僻的土地。
如果风车里郡战败,白马郡的铁骑就会从奥兰荒原踏过,从埋葬有英勇先烈的土地上踏过,死的人和活的人的灵魂再也不会得到安息。
争霸的郡国会在中央区点燃熊熊火焰,这道火焰会沿着平原的缺口一路蔓延到风车里郡的每一块领土,把本就不算富裕的沙土烧焦,烧得更加贫瘠,用在这贫瘠土地上生存的人们的尸骨炼出油水,一桶又一桶倒入炮车和嗡鸣的机器里。
给野狗一块骨头,肯定会被叼走,给人一点权力,他会变得野蛮。
风车里郡再没有独善其身的底气,只会沦为砧板上的一块肥美的肉,狼子野心的人们疯涌着上前,争夺啃食,大打出手。
战败国会被狼们分得精光,从土地到人口一点不剩。
他不能输。
风车里郡不能输。
唐顿深深吐出一口气,他尽量冷静地转动拨号盘,几秒的恍如隔世的忙音结束,他艰难开口:
“我同意,不过在签署条约前,你要把拉尔曼郡派来的三十万援军送来。”
对面带着笑意低低传来一句:“好。”
……
曙光迟迟不到来,天像是忘了吐白,一成不变的黑浓浓笼盖在每个人的头顶。
阿尔米亚手臂中弹,她撕下一截裙摆把手臂死死缠绕,防止失血过多而昏倒。
对比动辄使人变成断肢残骸的大炮,这处枪伤不值一提。
有个白马郡的士兵不死心地追逐她,已经打空了一把枪,他飞速蹲下来,从旁边的尸体怀里又抢来一把机。枪,子弹不要钱一样朝她洒来。
她觉得自己正在被一条疯狗追逐着。
他赤红着眼睛盯着她,眼珠子下方有几道擦伤,干涸的血迹从眼角斜着流下去,一直流到鼻子和下颌,血抢在子弹之前给他破了相,把一张过分瘦削的脸蛋一分为二,分成两半疯狂的画。
阿尔米亚在他身上感受到比以往任何一个敌军士兵还要汹涌的恨意。
她试着朝他的小腿开枪,但无济于事,他根本不在意受伤的小腿,借助恐怖的意志力一次次站起身,朝她跑来。
她又开了几枪,无一例外打在对方的小腿上。
但男人只是倒下了几分钟,又抓着泥土爬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