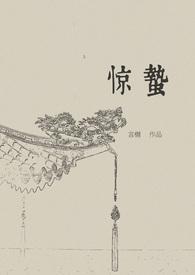无线文学>拉尔曼郡的魔女 > 90100(第12页)
90100(第12页)
加西亚紧紧咬着自己的胳膊动脉,几颗榴弹从他的身边窜过,大把大把的土灰溅到他脸上。
先前一颗飞炮落到他脚边,幸好他动作迅速,转身跑出十几米紧紧伏地,才不至于和坑中那几名尸体同眠。但是在奔跑的瞬间,他的手臂却被某个炮弹的碎片刺穿,皮肉肌腱割得一干二净,动脉被拉扯出来,血崩了他一脸。
他拼命咬住那道颤跳的动脉,用衣服袖子当做绳子当场捆死,近心端的血液开始变凉,剩下的半截手臂变得麻木,逐渐失去知觉。
这对他而言已经不算是疼痛,只是这份失去的知觉像是病毒感染一样,让他的脑子和身体都一并慢下来,端枪的动作也变得迟缓。
他抬头望,想在混乱中找到一个熟人的面孔,但是场面太过混乱了,他迟缓的脑神经无法一时解决这么纷杂的信息,也捕捉不到他的意图。
他踉踉跄跄站起来,刚走几步又被尸体的边角料撂倒,迎面扑进一个积血的浅坑里。
子弹擦着他的头发过去,他闻到后脑勺被烧焦的糊味。
他不敢抬头,只伸出一只手去探身边的高伦特步。枪,后面的士兵以为这是一个死人,踩着他的手指跑过,他的手深深陷入血泥之中,扭曲成得病的鸡爪,但他还在不死心地探,去探枪的边缘,去描摹枪柄轮廓。
他听到后方传来指挥官的喊话。
“第一个冲进敌方指挥营的士兵,连升五级!第一个折断敌军军旗的士兵,连升三级!割下一个敌军头颅,奖赏五百柳布!上不封顶!”
“拼一拼,大兵变少尉!少尉变大校!”
“取下敌军首颅的士兵,将由公爵亲自为他授勋!授予风车里郡最荣耀的勋章!最英勇的白银三角勋章!”
……
授勋是风车里郡每一位士兵最大的梦想,这是自祖辈就有的传统,是每一位士兵英勇无畏的象征,他们骨子里好战的血脉永远为此沸腾,为此奔涌,从不停歇。
他听到后方士兵呐喊的声音更加狂热了,一声声向前冲的口号仿若是撕破了喉咙吼出来的,饥饿使他们更有斗志,两眼发光,仇恨且狂热地看着每一位白马郡的敌人。
但他是拉尔曼郡的士兵,举目望去,全是激动疯狂的风车里士兵,找不着和他一样的外派援军。
泽沃角派来支援的少军团还剩下几个人呢?
在踏上这个战场之前,他连一个白马郡人都没见过,但此时,他需要抱着枪,把一颗颗锋利的子弹射入对方脆弱的胸膛,射入和他无冤无仇的陌生人的心脏。
他们中的大多数人,和他只见过这么一面,却就是决定生死的一面。
要说是仇恨吗?但他对白马郡人并没有仇恨,他只是住在遥远的,和白马郡并不接壤的雪国的一名普普通通的凡人。
白马郡的枪炮没有攻入拉尔曼郡的防线,战争的硝烟也只在邻国的土地上方弥漫,雪国永远飘着最纯洁无暇的雪花,一片片晶莹剔透,不会沾上一丁点血迹和硝灰。
那是什么把他送到了这片土地呢?
“今夜我们将占据拉麦尔麦颂的东线战壕!厨子们正在把千百万片面包和肉肠放入你们的铁餐盒!你们的杯子里装着风车里郡最香醇的酒,鱼子酱已经抹在面包上了!风车里最英勇的士兵们,军队有史以来最丰盛的晚宴就在前面等着你们!”
指挥官的声音从后方广播器里传来,滋滋啦啦的,嘹亮又刺耳。
他在催促着士兵们向前,但是敌军的重型炮和坦克需要用无数人的肉。体才能挡住。
面包不如授勋能撩动风车里士兵的心弦,对此刻的加西亚而言却是莫大的诱惑。
饥肠辘辘的肚子只在夜间短暂的拥有过两个土豆,消化后叛逆的扯着他的胃,不断紧缩,不断痉挛,饿得人肌肉抽搐。
那是什么把他送到了这片土地呢?
他回答:是战争,也是饥饿。
他手脚并用撑着站起来,手臂颤抖着举起枪,用瞄准镜望到一个正朝这边走来的士兵。
距离太近了,瞄准镜无法展现对方完整的身体,只强调出一张陌生的脸。
他穿着白马郡士兵特有的灰色军装,胸前紧紧缠绕着绷带,不断有他自己的血迹和别人的血迹染上去。
他用步。枪枪托上装着的刺刀扎入最近一人的心脏,拔。出来时毫不拖泥带水,那张陌生的脸上是熟悉的神情,一种对任何事物都无感漠然的表情。
神似的表情在战场上无数人的脸上出现过,仿佛他们都是被驯化出来的专门用以战争的武器,人类的身份只是伪装,在他们的眼底看不到对生命的敬畏,也看不到任何脆弱的温情。
灵长类生物与其他生物有别的怜悯之情彻底消失了。
冷血冷肺的灾厄在这样震撼的场面之前也会退缩,但一贯以审时度势著称的人类却飞扑着上前。
加西亚看着瞄准镜里走过来的男人,昏昏沉沉的大脑突然打了个寒颤。
他费力地托着枪,想要按动那个象征生死的机关,却被对方一把掀翻。
男人熟练地抱着枪,用枪托上的尖刀刺向敌人,却被地上人一个翻身躲过。
尖刀挑断了对方手臂上包扎的死结,手臂肱动脉的血飞溅出来,滚烫的液体钻入他的眼睛。
异物感过于强烈,男人下意识用手去挤了一下眼睛,加西亚就趁着这个机会滚入一旁的战壕坑。
他重重跌入两米深的战壕里,偏头死死咬住还在喷血的手臂动脉。
男人跳入战壕的声音无异于死神收割前敲响的丧钟,加西亚突然爆发一股潜力,用脸撑着粗糙疙瘩的土墙站起来,土墙里不断有锋利的子弹碎片和尖石头磨烂他的脸,但他已经来不及考虑这些了。
他一次又一次躲避敌人刺来的尖刀,大脑和身体连续不断向他发出预警,失血失觉的手臂和大腿就是全线崩溃的前兆。
每一次的呼吸都像是直接从肺里掏出来的一样,火辣辣烧着他的嗓子,如果此刻他能说话,他的声音一定比煤箱发出来的巨大噪声更刺耳难听。
尖刀刺穿了他的大腿,也扎入了他的左腹。
他却不能把身体弓成一条虾米的形状,这是最无害脆弱的婴儿在母体子宫里的动作,他现在身处战争腹地,没有温柔的母体给予他养料供应,也没有温暖的羊水舔舐他的伤口。
他只能强撑着站起来,一次又一次与死神决斗。
对面似乎已经恼怒他的垂死挣扎,不再用刺刀扎他,而是举起枪准备射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