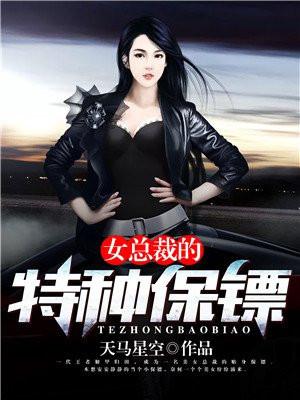无线文学>夺卿入怀 > 5060(第8页)
5060(第8页)
出于身体的本能,沈念当即推开郎君的肩膀,抵触着他的靠近,“淮之,莫要靠近,我怕……”
她的声音破碎而细碎,胸口起起伏伏,不停地大口呼吸着。
见状,宋淮之拉开距离,不敢再靠近她半分,心底泛几丝心疼,唇瓣用力抿了抿,“没事卿卿,别怕,我不碰你,你别怕,好不好?我不碰你。”
此刻,小姑娘就像是一只被暴雨淋透、瑟瑟发抖的雏鸟,可怜又脆弱。
平复几息后,她的身子终于不再发抖,抬眸望向宋淮之,她低垂着眼眸,声音带着几分沙哑:“对不起淮之,我还是不能——”
她还是不能和他行男女之事,
她还是害怕。
“这又不怪你,”宋淮之没敢伸手碰她,只坐在她身侧,柔声安慰:“卿卿,你会好的,一切都会好的。眼下不是已经比此前好多了么?我们都会好好的。”
沈念唇瓣微颤,欲言又止。
郎君说的没错,她刚到江南时,根本不能同他有任何亲密接触,莫要说亲她了,就是牵她的手,都会浑身发抖,窒息……自从有了这怪病后,宋淮之毫无怨言,小心翼翼地照顾她,带她慢慢走出阴影。
现在可以吻,可以抱,以后一定会慢慢走出来,与他做一对寻常夫妻。
她一定会好的。
“淮之我——”
可她还是觉得对不起他,
心底的那份愧疚像一股热流涌上心头。
宋淮之打断她的话,缓步走到案前拿出湿帕,轻轻擦去她额间的汗珠,语气平缓:“卿卿,莫要多说其他的,只要能陪在你身侧,等多久我都愿意。”
擦拭后,他又温声补充一句:
“你好好歇着,明日我去街市给你买桂花糕,你最爱吃的。”
沈念轻轻“嗯”了一声,乖乖缩在被褥里,只露出一个脑袋,看着郎君替她掖被角。
三年来,他少了些许稚气,多了几分成熟稳重。素色白衣,玉冠束发,唇畔的笑依旧温柔如清风。
她同郎君在一起,虽没有热烈的悸动,但却温馨平淡,总是让她心里暖暖的。
宋淮之看着她乖乖躺下后,便出了屋子去堂前抓药。
……
次日,沈念起身时,宋淮之已不在房中,她想着他定是买桂花糕去了,今日回春堂歇业,她便打算在家里安心等着郎君回来。
*
另一边,小巷的车舆里。
今日是帝王来江南的第五日。
裴争端坐在车内,不停地搓着玉扳指,眸底郁郁沉沉的,“宫里有什么消息?”
长戈躬身应道:“陛下,前朝倒是无事,不过小殿下那里有些棘手。”
“何事?”
帝王突然抬眸,眉头紧锁,言语中带着几分急切。
长戈如实回禀:“陛下,宫人传来消息,小殿下要娘亲已闹腾好几日,打碎了好些东西,至今仍未消停。”
“宫人实在不知该如何是好……”
提到娘亲二字,裴争先是垂下眼睫,而后抬眸直直地逼视着一旁的长戈,冷声道:“都是废物么?连一个三岁孩子都看不住?”
“昱儿若是出了事,都给朕去死。”
帝王点漆的眸子里带着些许寒意,长戈倒吸一口凉气,宫中那位小殿下从幼被帝王捧在手心里长大,尚在襁褓中就被封为太子,谁敢有半分忤逆?
“是,陛下,属下这便传信告知宫人,务必看护好小殿下。”
无形之中的压迫让车舆内的气氛愈发凝滞,长戈不由得打了个寒战,他试探性开口:
“陛下口渴么?不如下去喝盏茶?”
三年来,帝王情绪愈发不稳定,周身的戾气难以压制,他只好提出去喝盏茶,缓缓。
帝王轻轻“嗯”了一声,跟着长戈下了车舆,随后,他们寻了一处茶肆,要了一壶茶水。
此次出行本是微服私访,只为调查怀王乱党,但实际上裴争有私心,他想到江南瞧瞧。
小二端来茶水后,长戈在一旁侍立,轻声问道:“陛下,我们何时回京?”
眼下已在江南耽搁多日,怀王一事已调查清楚,若是再不回去,京中怕是要出大乱子。
裴争神色莫辨,指尖摩挲着茶盏边缘,淡淡说了一句:“明日,明日归京。”
“是,属下遵命。”
歇息片刻后,裴争在案上扔下银两便要离开,而就在这时,身前的摊位却忽然传来熟悉的人声。
“大娘,给我来一包桂花糕。”
已完结热门小说推荐
- 抖音新书让你去当炮灰女配,你怎么抢了女主剧本?陆临轩苏九陆临轩苏九
- 苏九转身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?找了五年的人好不容易回来,应该恭喜你才是。陆临轩噎住,苏九,你必须这么夹枪带棍一样跟我讲话吗?我们之间有什么交情?陆临轩这五年,苏家就像是一飞冲天,成了AI行业的独角兽企业,而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