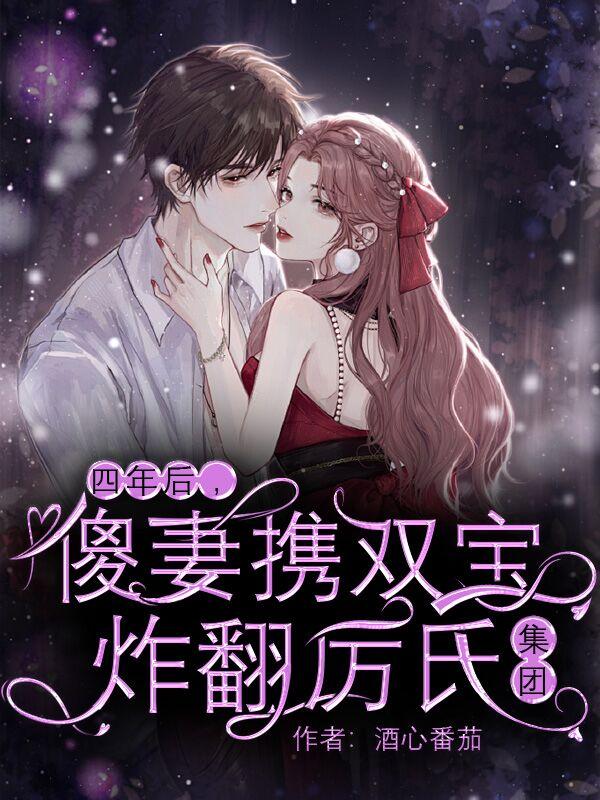无线文学>我在大秦种田养家 > 第199章 终章前夜教子孙麦穗传志留遗言(第1页)
第199章 终章前夜教子孙麦穗传志留遗言(第1页)
油灯的火光在墙上晃了一下,麦穗把青铜匣轻轻合上。她没再看它,只是用布巾裹好,放进行囊最底层。陶片上的符号还摊在桌上,阿禾画的兽皮卷也未收起,但她不再去碰。
她起身吹灭两支艾草香,只留一支在案头燃着。烟很淡,飘得慢。她走到门边拉开木栓,夜风立刻涌进来,带着田里的湿气。
她站在门口,等了不到一盏茶功夫,第一个妇人就到了。接着是第二个、第三个。二十个女人陆续走进夜读会的旧堂,脚底沾着泥,手里都抱着麻布包。她们不说话,依次在土台下坐下。
阿禾最后一个进来。她没坐,站到麦穗身侧,低声问:“都准备好了?”
麦穗点头。她从行囊里取出两捆东西。一捆是竹简,用红绳扎紧,封口贴着她的指印。另一捆是卷轴,外层裹着油布,边角有些磨损。
她把竹简放在案上,解开绳子,翻开第一页。上面写着《律注》两个字,笔画粗重,是她三十岁那年亲手刻的。
“这是第一版。”她说,“后来改过七次,加了种田的规矩、分水的法子、女子立户的条文。每一笔,都是咱们一块一块试出来的。”
她抬眼看台下的妇人。“有人记过账,有人量过地,有人守过渠。这书不是我一个人写的。”
一个年轻些的妇人站起来,双手交叠放在胸前:“我们愿意学,也愿意传。但……能不能只交给几个人?怕太多人乱改。”
麦穗走下土台,走到她面前,扶她坐下。“不行。谁都能改,谁都能加。要是只给几个人,那就又变成老爷们说了算。”
她转身走向卷轴,解开油布,展开一截。上面画着水渠走向、井位分布、坡度标记,密密麻麻全是线条和小字。
“这是《农产图》。”她说,“从赵家村开始,画到七乡十八屯。哪块地缺水,哪条沟能引流,都标着。你们每个人手里都有抄本,但这一份是母本,将来谁要修渠、开田、建晒场,都得照它来。”
她顿了顿,声音低了些:“我不一定能回来。”
堂内一下子静了。有人低头,有人攥紧了衣角。
“朝廷让我进京,领那个‘贤妇’金印。”她笑了笑,“他们觉得我听话,能当样子。可我知道,这一去,不一定还能回得来。”
阿禾站在角落,手按在腰间的匕柄上。她没说话,但眼神扫过每一个人,像是在确认什么。
麦穗重新走上土台,从行囊里拿出那个青铜匣。她没打开,只是把它放在竹简和卷轴中间。
“这里面有我看不懂的东西。”她说,“但它比我活得久。将来有一天,会有人认出它写的是什么。到那时,你们一起看。”
台下有个老妇人抹了眼泪:“您教我们识字、管账、定井位,现在又要走。我们……怕撑不住。”
麦穗慢慢走下来,蹲在她面前。这个女人姓李,二十年前旱年啃树皮活下来的,去年还在带头挖新渠。
“我不是让你们撑。”她说,“我是让你们自己站起来。你们已经不是谁的媳妇、谁的娘了。你们是定规矩的人,是划地界的人,是能让千亩田喝上水的人。”
她站起身,环视众人:“从今天起,夜读会不停。每月初一,你们聚一次。谁有新法子,拿来大家看。谁有问题,大家一起解。不准一个人闷着干,也不准一个人独占。”
没人说话。风吹动门帘,拍打着门框。
麦穗看了看天色。北斗已斜,离天亮还有两个时辰。
“走。”她说,“出去。”
二十个妇人跟着她走出屋子。阿禾最后关门,顺手把油布重新裹紧卷轴,抱在怀里。
她们沿着田埂往北走,一直走到麦穗祠前。那里立着一口铜钟,是去年秋收后集资铸的,钟身上刻着七乡所有参与共耕的女人的名字。
麦穗停下脚步,抬头看天。

![(历史衍生)[大唐]我的皇帝堂妹+番外](/img/84561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