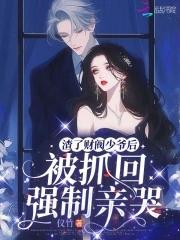无线文学>清安渡:四爷的现代小格格 > 第188章 栗泥暗码(第1页)
第188章 栗泥暗码(第1页)
姜岁晚合上那本画着双猫爪印的账册,指尖在朱砂勾过的肉垫上轻轻摩挲了一下。苏培盛推门进来,手里拎着个食盒:“格格,王爷让送碗栗子泥,说是您昨儿提过想吃。”
她没接话,只掀开盖子,舀了一勺送进嘴里。甜糯适中,火候刚好,连栗衣都没留一丝涩味。她咽下去,才开口:“谁做的?”
“小厨房新来的厨娘,叫翠枝。”苏培盛压低声音,“原是德妃娘娘那边遣过来的,说擅长江南点心。”
姜岁晚放下勺子,盯着碗底看了一会儿。釉色青灰,胎体厚实,是宫里常见的官窑款。她用指腹蹭了蹭碗沿内侧,又翻过来瞧底——一道浅痕,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。
“这碗,以前见过吗?”她问。
苏培盛凑近看了看:“像是库房里那批旧瓷器,去年清点时还剩十几件,后来全拨给小厨房用了。”
她点点头,没再多问,把碗搁在一旁,继续誊写云锦出入明细。苏培盛没走,站在边上等她吃完。她慢条斯理喝完最后一口,才把空碗递回去:“送去洗了吧,别磕了。”
苏培盛接过碗,转身要走,又被她叫住:“等等,碗底好像有东西,你拿灯照照。”
苏培盛愣了一下,真拿了盏油灯回来,蹲在桌边对着碗底照了半天,才“咦”了一声:“真有刻痕,六道,排得挺整齐。”
姜岁晚没动,只说:“记下来,回头我查查图谱。”
入夜后,她没睡,从床底下拖出个木箱,翻出一本《内府瓷录》,就着烛光一页页比对。翻到德妃私窑那章,她手指一顿——胎底暗刻六道弧线,形如猫爪肉垫排列,正是当年为避讳宫廷规制,特意改的标记。
她合上书,坐在床沿了会儿呆。窗外有脚步声,很轻,停在门外没动。她没出声,也没起身,只把瓷录塞回箱子,吹了灯躺下。
门被推开一条缝,胤禛站在门口,没进来,只低声说:“还没睡?”
“刚躺下。”她答。
他走进来,没点灯,径直走到桌边,放下一样东西。黑暗里看不清,只听纸张轻响。他说:“新账本封面,按你说的改了。”
她坐起来,摸黑过去,指尖触到封皮——凹凸感清晰,是猫爪印的轮廓,三道肉垫,尾巴绕圈,和她画的一模一样。
“你怎么知道我要这个?”她问。
“你画了两个。”他声音平静,“一个给我,一个给你。那这个,就当是第三个。”
她没说话,手指沿着纹路描了一遍。他站在旁边,也没动。过了会儿,她才开口:“碗底的刻痕,我查到了,是德妃私窑的标记。”
“嗯。”他应了一声,“继续查,别停。”
“你早知道?”她抬头。
“不知道。”他语气没变,“但你查的方向没错。”
她沉默片刻,把账本抱在怀里:“那我明天开始,从餐具入手,重新核一遍近半年的采买清单。”
“可以。”他说,“需要什么,让苏培盛去办。”
她点头,没再问。他转身要走,手搭上门框时又停住:“猫爪印,别画歪了。”
她忍不住笑出声:“知道了,四爷。”
门关上,脚步声远去。她重新点灯,翻开新账本,第一页空白处,她提笔画了个新的猫爪印——这次更圆润,尾巴多绕了半圈,像在打结。画完,她吹干墨迹,合上本子,塞进枕头底下。
第二天一早,她带着账本去库房。老账房正在整理瓷器清单,见她进来,忙起身行礼。她摆摆手,直接问:“去年拨给小厨房的那批旧碗,来源记录还在吗?”
老账房翻了半天,找出一张泛黄的单子:“在这儿,是从景仁宫库房调出来的,原属德妃娘娘赏赐之物。”
她接过单子,扫了一眼,又问:“当时是谁经手的?”
“是内务府的赵公公。”老账房压低声音,“不过那人上个月调去畅春园了,现在不在府里。”
她点点头,没再多问,只把单子折好收进袖袋。回厨房路上,苏培盛追上来:“格格,王爷让您去书房一趟。”
她没耽搁,直接去了。胤禛正在看折子,见她进来,指了指案头:“新送来的瓷器图样,你看看有没有眼熟的。”
她走过去,一张张翻。全是官窑新款,釉色鲜亮,纹样繁复,没有一件带暗刻。她翻到最后一页,顿住——图样角落有个小字标注:“仿前朝私窑制式,胎底可加刻”。
她抬头看他:“这是什么意思?”
“意思是,有人想借旧器传新信。”他合上折子,“你擦的碗,只是开始。”
她没接话,只把图样放回原处。他看着她:“怕了?”
“不怕。”她答得干脆,“就是觉得,画猫爪印比查瓷器轻松多了。”
他嘴角动了一下,没笑出来,只说:“那就继续画。画够了,我给你换鱼。”
她没忍住,笑了:“鱼尾巴难画,容易画成蛇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