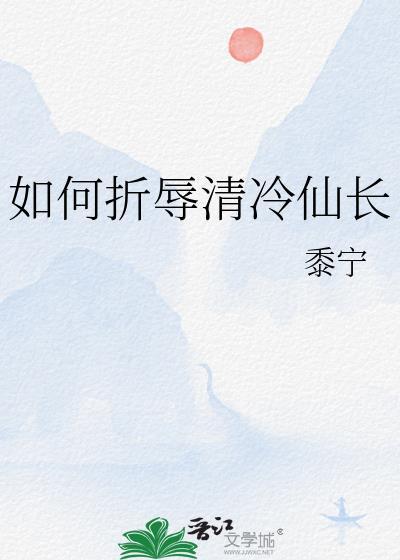无线文学>听见 > chapter31(第1页)
chapter31(第1页)
chapter31
“该怎麽说呢……”池玗摇了摇头,声音也沉,“以前确实太天真,活该吃点苦头。现在好了,现在,不会去信那些了。”
要经历过什麽,曾经抱有的期待才会被彻底磨灭呢?这点,沈星河是感同身受的。
沈星河不善言辞,只能在夜里尽可能的靠在池玗怀里,获得慰藉的同时也用自己的方式许下承诺。
“除了那些穿白褂子的人,其他,也还好吧。我那室友挺有意思,他自称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,但也许我比较庸俗,看不懂。”
沈星河放的电影声音很小,几乎成了默片,他也根本没看,一直在听着身後的池玗说话。
池玗用下巴轻轻蹭着他的发顶,目光追着他偶尔移动的手指,无声笑了笑,“哥喜欢看这个电影?”
屏幕瞬间暗去,沈星河擡起头,说:“我在听你说话,没看进去,它讲了什麽?”
“……我也没看。”
沈星河向来不擅长撒谎,这份坦诚有时候让池玗有些不知道该怎麽接话。
池玗苦恼了点,沈星河放下手机把他手擡起,指尖顺着上面浅淡的纹路轻轻抚摸过去,“池玗,有恨是正常的。你不是一定要做个乖孩子。”
他转过身,把池玗轻轻推倒在床上,低头吻在他额头,“在我这里乖一点就够了。”
望着沈星河强装镇定的脸,池玗终究没忍住,灯光也晃得他闭上眼笑出了声,“好了,哥,我没那麽脆弱。你不要强迫自己来安慰我——应该是我来爱你,我欠你好多啊。”
沈星河无言,很快他又被拉着坠入池玗怀中,听他在耳边喊着名字。
“……你名字很好听,我以前一直觉得,他就不像存在于现实中的。有人好没礼貌,他们说你的名字就是电视剧里抓出来的,没什麽意义。爷爷都告诉我了,我记着呢。”
各得其光,汇流成河。沈老爷子说,盼他容得下不同学问,也容得下各异人心。
“好长一段时间,我一直都不敢喊出口,不然他们又有机会给我开药。所以现在多叫两声。”
沈星河小声应着。他其实一眼就能分辨出池玗现在是强装还是故意示弱。但他不介意去迎合,需要他迎合的人并不多,池玗现在是唯一一个。
其实在疗养院里,如果池玗一直保持沉默,或许会少吃很多苦,回想起来,他承认那时候确实不够沉着。因为无法忍受那些荒谬的“诊断”,他会出言反驳,而那些人只是冷冷看着他,然後轻描淡写下结论:你需要接受更多治疗。
他们说,他就像他父母说的一样,本质桀骜难驯,因此需要“特别关照”,而那些说是轻微的电击疗法只是必要手段。
次数多了,池玗觉得那边和家里其实没有本质区别——只是疼痛更具体,更血肉分明。
有天回到狭小的房间,池玗看见室友手里拉着几根金属琴弦,对方看到他,又慌忙地藏起。
池玗第一次主动开口,承诺不会告密,于是他得以短暂地和它们相处一晚。他把那几根琴弦绷紧在桌面,弹了一出错漏百出的旋律。
室友激动地宣称:“你一定是这世界上另一个天才!”
“……那,还有一个?”
“当然是我。”他拍着胸脯,眼睛望向那小小一扇窗,“我知道宇宙里所有物质的运转规律,包括琴弦。所以我当然是天才。”
池玗笑不出来,强忍着手上持续的胀痛麻痹,在被迫服下的药物副作用中不甘地闭上眼。又再半夜醒来,压抑着颤抖把琴弦紧绕在手腕上,出血带着痛,他才如梦初醒似的制止自己的行为。
这件事没有藏好,第二天他被推去见老院长,接受关于昨晚声音来源的询问。
毫不意外,池玗又被处罚,却没再吭声。
一年後他们才改口,说他“进步显着”。甚至在某年圣诞夜,在一楼大厅举行的晚会上递给他一把老旧的小提琴,池玗竟然荒诞地又成了焦点。
“睡吧。”沈星河小声说。
“哥。”池玗忽然问,“你现在对我,更多是同情,还是别的什麽?”
沈星河将脸贴在他颈边,几乎一字一顿:“我有什麽资格同情你。你不是来爱我的吗,我也该有同等的回应。”
他们现在有谁高人一等吗?似乎都是两手空空。
池玗在黑暗中低低笑着,心满意足。他捞过被子,一翻身将沈星河紧紧搂入怀中。
一片漆黑,沈星河什麽都看不清,只有身上的热意是源源不断的。
随後他听见池玗带着希冀,又小心翼翼地问:“哥,我如今没有功成名就,还和我走吗?”
五年前机场分别时,池玗问过类似的话,沈星河当时心怀忐忑,但还是回答:带我走吧。
时过境迁,池玗失去了一切,他也一无所有,唯独这个人还在。
他摸索着抓住池玗一只手按在胸口,深深吸了一口气,声音清晰起来:“带我走吧。”
第二天池玗依旧起得早,沈星河的生物钟混乱不堪,虽然困还是跟着起了床。
蓟城格外冷,却总找不到冷的源头,街边行道树都打着颤。
沈星河坐在街边的早餐铺,小口喝着过分甜腻的粥,食欲不振。
池玗接到艾列维消息,说池叙乔暄现在就在律所,要求他亲自过去,池玗只能表示他需要半个多小时的车程以及一顿早饭时间。
沈星河本意不想听,池玗面上也并不想让他听,手机却凑得越来越近。
他索性拿过电话,温吞地对艾列维说:“我们马上出发。”
挂了电话,看着低头闷笑的人,沈星河无奈——池玗总恨不得向所有人宣告他们的关系,这点一直没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