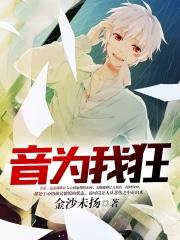无线文学>重生1958,扛枪打猎带富全村 > 第211章 蚕蜕那晚全村点了长明灯(第1页)
第211章 蚕蜕那晚全村点了长明灯(第1页)
林英的指尖悬在竹匾上方半寸处,月光从窗纸的破洞漏进来,在三十枚珍珠色的蚕茧上投下细碎光斑,像星子落进霜瓷盘中。
青囊子的声音仿佛从寒潭深处浮起的冰碴,顺着她后颈缓缓爬入耳道:
“寒蚕蜕壳之夜,吐丝最净,蜕皮最寒,正是‘五引’最后一味。”
她盘坐在草席上,腰背绷得像拉满的弓。
这是她守在寒蚕房的第三夜,玉坠贴在胸口,那道细微的裂纹随着心跳一下下刺痛,像根烧红的针在皮肉里挑。
她虽未入空间,却以玉坠为引,将自身性命与寒蚕同频,外界每过一刻,她的气血就被抽走一分。
昨日给小药渣喂丹时,喉头涌上的腥甜便是代价,可她生生咽了回去,血沫黏在舌根,泛着铁锈味。
“光……在动。”
竹门“吱呀”轻响,网伢子缩着脖子挤进来,冻得通红的鼻尖几乎要碰到竹匾。
这孩子原是个聋子,被林英用空间里的野山参吊回半条命后,竟生出了双“天眼”,能看见常人看不见的气,闻得到隔山的风。
此刻他仰着脸,眼瞳里映着茧上流转的微光,像水底游动的银鱼,“像蚕要醒了。”
林英攥紧腰间的短刀,刀鞘是野猪皮鞣制的,边角早已磨得亮,如同她这些年的隐忍。
子时三刻的梆子声刚在村口响过,第一枚蚕茧突然颤了颤,比蚊鸣还轻的“嘶啦”声里,银丝裂开道细缝。
一只半透明的幼蚕缓缓爬出,旧壳留在茧中,泛着若有若无的金纹,那是寒蚕毕生的寒毒,全凝在这层皮里了。
她抄起冰玉匣,玉勺在掌心沁出冷汗,指尖触到匣沿时,一阵刺骨寒意顺着手腕窜上肩胛,仿佛有冰蛇钻进了血脉。
第一枚蜕壳刚入匣,颈间玉坠“嗡”地剧震,寒潭的水线在意识里疯狂下降,半尺,一尺……她咬得后槽牙疼,耳边嗡嗡响着青囊子的话:“你救十人,损寿一载。”
可当她想起小药渣烧得滚烫的身子,想起王婶跪在祠堂前磕得额头青肿,这疼便成了钝钝的,像块烧红的炭焐在胸口,她这条命,本就是捡来的。
第三枚蜕壳入匣时,窗外的雪粒突然大了,扑簌簌砸在茅屋顶上,像谁在撒盐。
林英的指尖沾了血,是刚才取茧时被冰玉划破的,血珠落进匣里,竟“滋”地一声融了,在寒蜕上晕开淡红的雾。
她没察觉,直到第七枚茧裂开,眼前突然黑,扶着土墙的手直往下滑。
“林队长!”
火炉婆的声音像口响钟,撞得耳膜生疼。
老灶妇不知何时站在门口,裹着的蓝布衫还沾着灶灰,布满裂纹的手稳稳托住她后腰:“火不能熄,人不能倒。”
她指了指村东头的灶房,青烟正从烟囱里钻出来,绕着房梁缠成细缕,“五药引我按那白胡子说的比例下了瓮,松脂火煨着,我盯着呢。”
林英这才注意到,火炉婆的眼尾全是红血丝,眼角还沾着块黑灰,她定是三日没合眼了。
老妇把怀里的粗陶碗塞给她:“喝口热姜茶,我烧了一辈子灶,还没见过药能开花。”
姜茶的热气扑在脸上,湿漉漉地黏住睫毛,辛辣的气息冲进鼻腔,舌尖尝到一丝焦糖般的回甘。
而就在同一时刻,村外柴垛后,一双眼睛正死死盯着灶房草帘缝隙透出的火光。
赵德海的徒弟蜷在雪中,鼻涕冻成冰线,看火炉婆掀开草帘,火光映得她脸上的皱纹都在跳。
瓮里的药汁“咕嘟咕嘟”响,突然“噗”地一声,一朵金莲花从瓮口浮起来,花瓣上还沾着水珠,三息后才“啪”地散成青烟。
他裤裆一热,连滚带爬跑回县城时,鞋都跑丢了一只。
“师父!”徒弟跪在赵德海跟前直哆嗦,“那火里……真开了花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