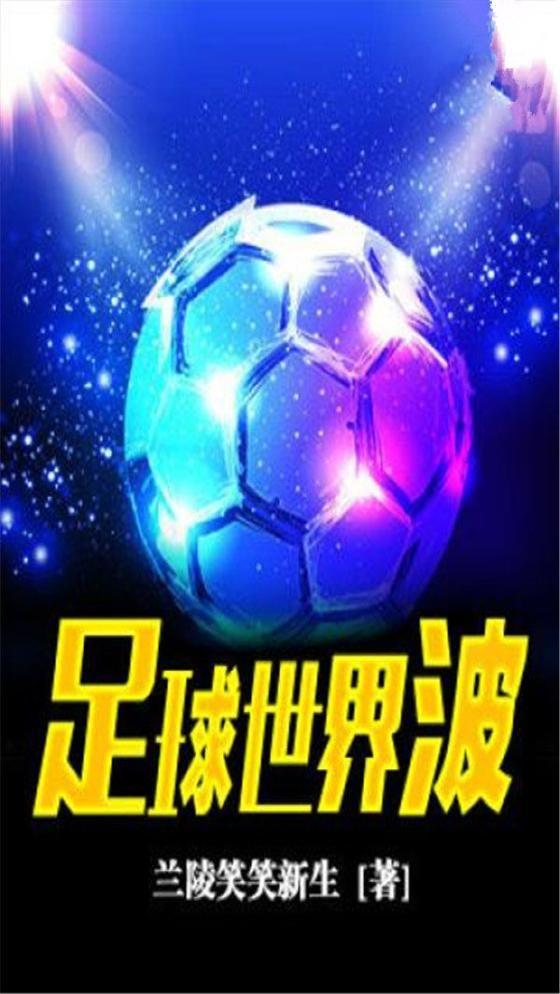无线文学>主人的任务罢了 > 番外 2他的转变(第2页)
番外 2他的转变(第2页)
“脱!”他沙哑地命令道,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霸道。
女孩吓得脸色白,却不敢违抗,颤抖着双手,笨拙地解开衣服的纽扣。
李泽丝毫没有怜惜,他直接上手,粗鲁地扯开她的衣服,扣子噼里啪啦地崩落,瞬间便将她那件薄薄的衣衫撕扯得七零八落。
女孩的身体彻底暴露在他的眼前。
她有着娇小的身躯,皮肤白皙细腻,胸前的乳房虽然不大,却显得挺拔而饱满,两颗突起的乳尖因羞耻和寒意而微微泛红。
她那双纤细修长的双腿,此刻紧紧地并拢着,试图遮掩住那片私密的花园。
李泽的目光冰冷而锐利,他的手毫不犹豫地伸向她那片布满娇羞与恐惧的私处。
他粗鲁地剥下她那件蕾丝内裤,露出她那片尚未被开的、充满了青春气息的私秘地带。
女孩的阴毛稀疏而柔软,皮肤白皙,阴唇粉嫩,尚未被情欲浸染,显得异常的娇嫩。
他喘着粗气,眼中燃烧着征服的欲望。
他解开自己的裤子,将早已勃起、坚硬如铁的肉棒暴露在空气中,那粗大的青筋暴突,预示着一场即将到来的狂野。
他抓住女孩的纤细腰肢,将她强行掰开双腿,然后抵住她的花蕊,凶狠地,却没有一丝怜惜地,猛地长驱直入。
女孩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,身体因剧烈的疼痛而猛地弓起,眼泪瞬间夺眶而出。
她试图挣扎,但李泽的力气太大,她根本无法反抗。
她只能紧紧地抓着地毯,任由那股剧烈的刺痛,如同潮水般将她彻底吞噬。
李泽的肉棒感受到那紧窄的包裹,那份强烈的挤压感激了他更深层的兽性。
他没有丝毫停顿,在女孩持续的惨叫声中,开始猛烈地、毫无节奏地冲撞着,每一次都伴随着皮肉撞击的沉闷声响,毫不留情地贯穿她的身体。
小哈哈大笑,看着李泽这副狂野的模样,眼中充满了认同的快意。
他加快了自己身下女人的动作,两人在糜烂的包厢里,上演着一场充满酒气与欲望的狂欢。
……
自从那次在会所的放纵,李泽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
他现自己隐隐喜欢上这种牢牢掌控他人的感觉,喜欢看到那些平时娇滴滴、眼神怯懦的女孩,在他的身体下,因为疼痛和快感而扭曲变形的表情。
他享受她们口中细碎的求饶,享受她们被他粗暴对待后,依然要强颜欢笑的卑微。
他食髓知味,背着程雨晴,变得频繁地出入那些隐秘的会所。
奢华的包厢里,弥漫着烟酒和荷尔蒙的气息。
他看着那些年轻貌美、穿着暴露的陪酒女,像母狗一样温顺地服侍着他。
她们谄媚的笑容,刻意迎合的娇媚,以及在他金钱攻势下,被逼着摆出各种羞耻姿态的模样,都让他欲罢不能。
那种纯粹的,基于权力和金钱的控制,带来了无上的快感。
他可以随意地命令她们跪在自己身下,含弄自己的肉棒;可以随意地让她们张开双腿,让她们被自己粗暴地贯穿,看着她们眼含泪水却又不敢反抗的样子,那种感觉,就如同神明一般,主宰着另一个人的身体和意志。
然而,渐渐地,一种空虚而无趣的感觉,也开始在李泽的心头滋生。
这些女孩,她们的顺从是如此轻易,她们的身体是如此廉价。
她们没有灵魂,没有情感,她们只是一个个可以随意买卖、随意亵玩的人偶罢了。
他的目光在一次次狂欢中,不自觉地又回到了程雨晴身上。
她是他真心爱过的女人,是他曾认定要相守一生的伴侣。
她的清纯,她的温柔,她的体贴,以及她第一次在自己身下绽放时的娇羞,都深深地刻在他的骨子里。
他想起她第一次被他插入时,那双因为疼痛而流泪、却又充满了深情的眼睛;他想起她高潮时,身不由己地弓起身子,哭喊着他的名字,声音破碎而黏腻。
要是他最爱的雨晴也能这样呢?
这个念头,像一颗带着剧毒的罂粟种子,一旦种下,便疯狂地在他心头蔓延开来。
如果,如果他能像对待会所里的那些“母狗”一样,看到程雨晴在他身下,因为痛苦、羞耻却又无法遏制的快感而神魂颠倒;如果,如果她也能像那些女孩一样,强颜欢笑,卑微地屈从于他的所有命令,但那份顺从,不是因为金钱,而是出于对他的爱,对他的依恋,对他的无法割舍……
李泽的呼吸变得粗重。
他想象着程雨晴那张清纯的脸蛋上,沾染上情欲的红晕和被羞辱后的迷茫;他想象着她那双温柔的杏眼,被他逼迫着,带着哭泣,却又充满魅惑地凝视着他;他想象着她的身体,曾经那么纯洁、那么高傲,在他面前彻底沦陷,成为一个只知道承欢的“玩物”。
那种极致的控制欲、占有欲,以及掺杂着偏执和畸形的爱,如同洪水猛兽般,瞬间将他理智的堤坝冲垮。
他突然开始觉得,那些会所里的女人索然无味,只有程雨晴,她才是最有价值的“猎物”,她才是唯一能满足他内心深处欲望的人。
他知道,这很病态,这很疯狂。
但他已经无法自拔。
他想把她变成只属于他一个人的“花瓶”,一个可以任由他肆意玩弄、任意摆布的“尤物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