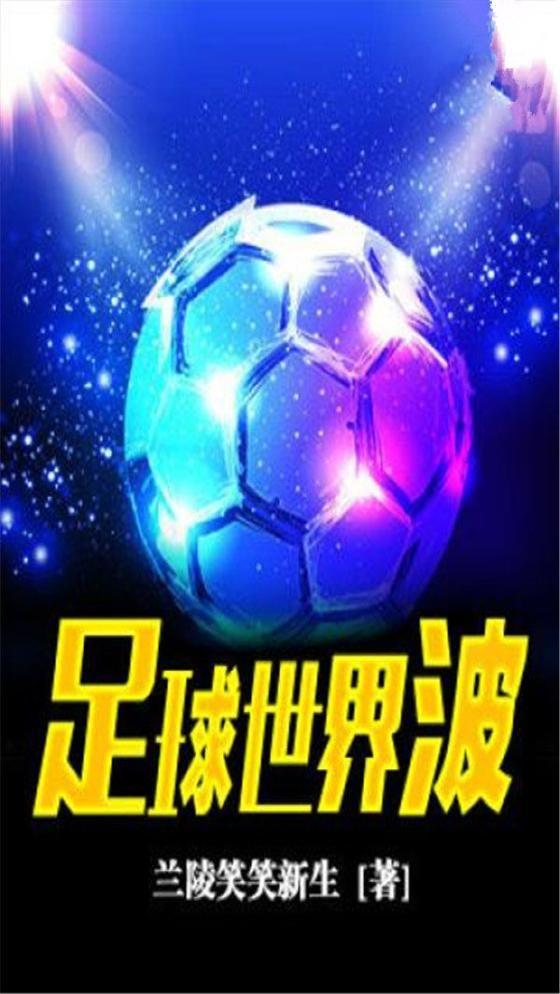无线文学>孀妇 > 100110(第6页)
100110(第6页)
他身量比她高出太多,迈的步子自然也更大,加上步伐疾快,她只得踉跄被半搂着往前。
郦兰心恓惶失色,可身子疲酸发软,根本没力气挣开,须臾眨眼,被推入方离开没两个时辰的榻上。
正当惊而生惧,以为他又要行恶时,肩头有兀地被握住,身子被抬拉坐正,双手被紧捉住。
男人掰开她双手掌心,将那根裙带塞入她手里,而后迫她攥着。
迎着她难以置信的惊慌目光,他将衣领处向下扯了几分,从脖后延伸至侧边的红紫深痕清晰可见,如同烈犬项上环圈。
郦兰心呼吸一窒,瞳中紧缩。
宗懔笑不及眼底:“昨晚,你拿着这根东西,勒著我,叫着要脐馬,——,现在想起来要躲了?”
短短几句,却如蛇露尖牙,蝎摆尾钩,毒液咬着肉钻入血脉经络后,神智躯体骤然僵硬震悚。
瞳仁都动不了分毫,呆呆握着手心里的裙带,满面迷惘空白,惊愕无措。
而站在她跟前的人却犹未满意,不肯放过她,欺身上来,捏着她的手。
她人是木的,魂是僵的,只能像软泥捏的偶人一样被他牵引着动作。
她坐在榻上,而他半跪在榻边金漆踏床上,较她低一点。
他掌心托着她的小臂,缓缓向上抬起。
她檀口張着,吐氣时越来越抖,越来越顫,眼睛一动不动,就这么被他带着,双手攥着裙带,绕到了他的脖后。
他的眼睛直直凝视着她,沉幽晦暗,在裙带轻贴住他脖颈时,她咽间忽地轻动。
仿佛着了魔,又抑或是长久埋藏的幽魂附了她躯体,雙膝併絞起来。
手不受控制地,缓缓,拉紧。
如同牵动一头野性难驯的兽,而此时支配的缰绳只在她一人手中。
男人顺着势,被拉扯到她面前,额贴着额,呼息糅著呼息。
鼻尖探著觸碰,他面色沉沉,掀唇一隙:“……姊姊,張嘴。”
她兀地輕悶出一聲低低黏泣,頭腦混亂,脣辦分离,軟红下意识地如往常一般伸出。
蛇攪津混至悶窒,方才神智微醒。
郦兰心猛地松了手,偏首躲避,颊泛了红,喘着气颤咳。
裙带被顺势甩落至一旁,快要掉落榻下。
宗懔抬手,轻笑抹了唇角,而后握住她肩头,压至她耳畔,气声:“现在肯认了?”
“昨日在榻上脐了兩回馬,叫了水來,又非得再脐什麼水牛,”沉沉低语,“我从前都不知,姊姊有这般喜好。”
“下回,咱们……”轻笑着。
他廝磨著她耳鬓,没瞧见她脸色霎时青白惊红交加,整个人都在打战。
郦兰心紧闭着眼,只觉天地倒悬,五脏六腑狂跳。
在听到“水牛”两个字的时候,更是恨不能立刻昏死过去。
此时她真是无比想要回到昨晚,回到晚膳的时候。
要是能回去,她一定要把那桌上的酒膳全给一把火烧了,一挥手砸了,那些个东西,真是要害死她了!
也顾不上什么惧不惧怕不怕了,现下唯一充盈脑海不断盘旋翻滚的只一个念头——
她怎么会,怎么会,做出这些事的!
拿裙帶……
还,还脐……
是她干的?
都是她干的?
便是此刻,耳边还源源不断钻进来熱息黏语,郦兰心眼睛闭得越来越近,呼吸越来越急。
一点红从颊蒸遍了头脸,全然如过年时包着糖蜜的喜纸。
下一刻,猛地摇头,把贴着自己的人一把推开!
宗懔猝不及防,被她推得向后仰去,但很快稳住身形。
拧眉:“姊姊?”
郦兰心臊得头都不想抬,更不敢看他,生怕一抬眼,又看见他脖子上她弄出来的痕迹。
低着头不说话,手攥紧裙摆。
宗懔看着她突然变脸,又开始逃避的模样,顿了一瞬,而后直接气笑了。
冷笑着:“姊姊,你对我做了那样的事,还想翻脸就当忘了?”
郦兰心呼吸急促。
他自然不会就这么放过她,笑里带着鸷戾:“你昨夜说的那些,你是都不肯认了?要我一一再说给你听么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