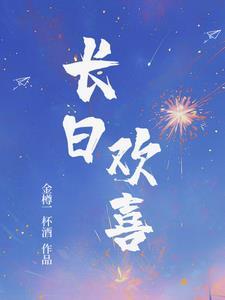无线文学>[红楼] 不二臣 > 第156章(第1页)
第156章(第1页)
而第一次的相见更佐证了她的想法,自那以后,不常见人的州牧夫人给外界打了个缺口,杨府的大姑娘登门最多。
然而今日,她虽仍偎着黛玉坐,样子却有些闪躲。
窗外漏进来些‘咦咦啊啊’的唱腔,里面的词是淮越方言,黛玉听不很懂,只捡着些‘天’、‘神女’、‘花’这般的话,知道唱的还是跟昨天一样——但调子怎么又变了?
偶尔有人叫那婆子收声,免得惊扰客人。那婆子记住一会,没多会又忘了,依旧唱着,坐在院子里做些针线活。
这歌总是不连贯。
桌上的点心还是京城中吃惯了的样式,杨芷喜欢,黛玉便没有再更换。府上的婆子议论过杨治中府上的公子姑娘,说小小年纪失去母亲多么可怜,又说不知道杨治中会娶什么样的继夫人。
杨治中没说过一定不娶,落在旁人眼中就是一定会娶。可黛玉看着对面女孩的发顶,忽然想若是那位杨大人要娶,如今也不会这边担忧儿女往外祖家去的事。
杨芷的脑袋一直垂着,和她从前灵动活泼的样子区别很大。黛玉端起茶盏呡一口,见小姑娘还是专心品鉴那一块已经吃了很久的点心,不禁笑道:“这是怕我也做了你父亲的说客?”
“这却不是。。。。。。不全是。”杨芷的那块糕点只塌下一只角,上面的粉花纹丝未变。她自个静默一会,听着窗外的唱词,直到确定那婆子彻底遗忘这一回事才开口。
“我只是怕自己狠不下心,别人再略一说说,就。。。。。。”
她这会又不吭声,眼角垂下,是她这样年纪的女孩常有的撒娇样子,这会做来却无端有几分可怜相。
面前栽了庄稼的花盆上雕着铁线莲——黛玉问府里婆子要一只花盆,那婆子便精心择选一个描了花,样子又茂盛的给她——这花盆约莫不是淮越当地制作,淮越没有这种花,当地的工匠想来也不会特意描画。
黛玉慢慢将身子伏低,透过越发茂盛的枝叶,看着叶芽后另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。
“等过会子就要把它移到院子里,一直在花盆里养着,再不移开,根就扎不深,养不大。”
更细嫩的指头触在叶子上,叶子颤抖,花苞点头,好像芯子正蒙在瓣朵里‘呜呜’哭。
“夫人,我不知道自己要不要走。”
“你第一次来见我,就跟我说过,不想离开淮越。”黛玉伸手抚一下杨芷的鬓角,那稚嫩的脸颊有些冰凉,声音却强作大人模样。
“是,我不想走,可我还有弟弟妹妹呢。”杨芷坐直身子,朝向黛玉,眼睛却没有落在任何一个方向:“我已经失了母亲教养两年,再拖延,即便妹妹之后去了金陵,也要多遭一层嫌弃的。”
“而弟弟去金陵,能得更好的师父。即便是金陵外祖家的族学,想来也比淮越的好上许多。”杨芷想了想,又记起父亲惯常用的说辞,道:“沈大人也是到了京里,才拜了天下闻名的斐先生的呀。”
她说完才觉失言,缩一下下巴,怯怯朝黛玉看来。
“这话不假。”黛玉的手还停留在杨芷的面颊,她为这小女孩的话有几分恍惚,心说怎么这样的缘由几十年都不曾更换。可那无措与茫然又真切叠在她面前,叫她想起许多年前的扬州,那一日离岸的垂柳也是这样摇摆。
“可若是再叫择选,却无论是我还是沈大人,都不舍得离开扬州。”这一句话伴着旧时乡音脱口,这句话曾许多次出现在黛玉与林言的谈话中。
——半嬉闹的,半认真的,他们总是这样说。
若是能预知将来,不如一开始就不要走。
早知最后仍是他们二人在一处,就不该被那些话绊住,该一直留在扬州,留在父亲身边。。。。。。
世人说沈大人是去了京城才拜下大儒,这话不假,但他掌心上手板落下的印痕比常年提笔的痕迹更重。
斐先生当然是爱护徒弟的师父,林言今日的成绩拋不开他的辛苦。
有舍有得,有得有舍,只看心里哪一方更重。
杨芷怔怔望着黛玉,不知为何更加想哭。
停留在颊边的温度漫上眼底,指肚温柔地将水滴收拢。
“我不想离开父亲,离开淮越——可我不走,我弟弟妹妹也不肯走,我怕她们被我耽搁。。。。。。”
“你妹妹暂不好说,但你弟弟只晚你一年生。这里面的干系,他未必就是懵懂。”帕子被温水浸润,蘸去小姑娘脸上的泪珠,黛玉忽然想起林言修建的书塾。
“你若惦记此事,不妨将你妹妹也带来府中。我虽当不上‘教导’,但在州牧府中,想来也少叫人说嘴了。”
“那若是夫人您当年留下,又会怎么做呢?”其实杨芷心中已有关于去留的定论,只是芽根不牢,还未深扎土中,自己也随和了外界的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