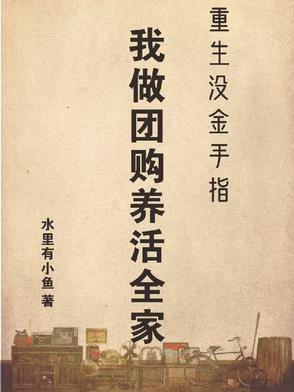无线文学>[红楼] 不二臣 > 第152章(第2页)
第152章(第2页)
杨治中职位不低,但自他夫人辞世,杨家便也有一二年被各家夫人‘忘记’。
自有夫人惦记着与先夫人的情谊,私底下常常照顾杨芷姊弟三人——只是杨芷的年纪太小,总还太小。。。。。。
晨阳斜照,杨芷椅在窗户底下,周嬷嬷正在给她绾头发。那是杨芷的母亲留下的心腹人,先夫人辞世后也没有离开,依旧留在杨府里照顾这三个孩子。
她总说:“长姐如母”。
杨芷拨弄着桌上的一只素色珠花,她今日起得太早。小妹妹离不得她,这会正盘在她膝盖上,仍睡着。
脚尖提起,杨芷颠荡两下腿,觉得小妹真是在长大,又重了。
今年秋,小妹整满三岁,她也有九岁了。
眼前的那只素色珠花被周嬷嬷拿起来,她偎在杨芷耳边,轻声道:“前两年二姑娘身体不好,这会养得胖了些,路上也安心。”
“爹爹还没说要我们去呢。”
“老爷怎么会没这个想头?虽说现在州牧夫人多喜爱你,但总不是长久的事。”周嬷嬷的手指拂过杨芷的后脖颈,冰冷的触感激得她一瑟缩。可周嬷嬷并没有发觉杨芷这时的不自在,她仔细把珠花簪戴到合适的位置,更压低声音道:“老爷往后续娶,约莫也是当地的门户。到时候姑娘三个。。。。。。总还是亲外祖好上许多。”
没等杨芷吱声,周嬷嬷兀自道:“到了金陵,到了老太爷府上——姑娘们有得环配穿戴,又得个有教育的名声,将来好出嫁。哥儿呢,也能拜好师父,不至于在这穷苦地方跟着捱。”
顶上的声音一道连一道压下来,直到怀里的妹妹偏一下脑袋。若是从前,杨芷大约会暗地里松口气,借机摇头示意周嬷嬷不要再说。
但这一回,她只是扭了脸,平静道:“弟弟若要走,便叫他走。金陵学堂有他的好处,又不收我一个女学生。”
“我不走,我就在淮越,哪里也不去。”
这个清晨不只有杨芷在忙碌。
张家二爷的媳妇,人称博二奶奶的,落在任一人的口里都很‘乖’。她从前也跟官家夫人见过,跟着大嫂,并不需要事事出头。这在从前是她的好处,但当张家大爷一病死了之后,就显得很不中看。
掠动的车帘做了碧波荡漾的湖,博二奶奶隐在帘后,像溺在水底的鬼在朝外看。她隐约望见官邸飞扬起来的屋角,心里窃窃想着那新来的州牧夫人是否也跟上一任那般‘讲规矩’呢。
她也曾来过州牧的官邸,但叫她意外的是这会再见竟没什么大的改变。新上任的官员大多想除一除前任的‘晦气’,尤其当前任的离开的原因并不光彩。
但现今这位显然不计较这样的事,博二奶奶跟着引路婆子往前走,不自觉观察起周遭景观。
是因为自忖宗亲,无论如何都受不得害。还是因为心中本不迷信官场风水,坤上巽下只作笑谈?
她抿抿嘴,实在很期望是后一个原因,但她也知道,大多数人都是‘宁可信其有’的。
应下她帖子的夫人并没有给出下马威的意图,这一路上丫鬟婆子只有笑颜,没有提点——可是实际上,单这位夫人答应见她这件事就足够叫博二奶奶觉得很意外,可能是因为她的公公在淮越冒尖,可能。。。。。。
眼前的门帘子水一样荡开,屋子里的温度太舒适,一瞬间叫她觉得自己是刚从水底挣出来。
那年轻的林夫人轻轻唤了声什么,应当是她自己写在帖子上的称呼,这会听来却不清晰,生疏得奇怪。
黛玉请博二奶奶坐下,请她喝茶,跟她漫无边际地聊着天。对面女子的声音是如她写下的文字般轻缓细致,眉眼看去像拓印下的仕女图。但时时低着头,看去下巴太尖,说不清究竟是什么脸型。
她的肩膀上从始至终架着一杆无形的秤。
“原说早先该应承好意,奈何身子不大争气。”
“哪里的话,淮越湿热。夫人千里迢迢来到这边,一开始难免不适应。”博二奶奶半抬起脸,不知怎么,下巴仍是收着,看起来十分谦逊:“倒是我们,前些日子还自己责怪,说不该这样急火火地邀请,该再
多准备好些,也叫夫人习惯当地。赶巧正苦恼的时候,夫人就体贴,没叫我们为难。”
这谈话不避讳谁,启开着窗户,博二奶奶窥见外面玛瑙蓝的天上擦过一段残云——短、直,刺扎扎的,没什么遮掩反叫她不自在。
黛玉也顺着她的目光朝外面看,淮越一带多雨又闷热,每下一场,都很迅速地闷干。目之所及的墙面总都是淡淡的黄,不均匀,天然是一片写意的流派。他们居室的院子里种着一棵积年的槐树,在这入秋的时节也不吝啬情义,以至于绿得有些吵闹。
那一片片叶子映着淡黄,倒显着几分肃穆,总之不像张家的那些肥厚舌头。博二奶奶看得有些出神,忽然,叶子在树梢也看到她,招招手,转眼就敲窗来了。
博二奶奶被惊一跳,忙不迭收回视线,却见林夫人依旧笑着,拿一把小剪子修着盆里的绿植。
她又被这植物勾了眼睛。
“夫人这花好精巧,似不常见到。”她说得很谨慎,略伏低身子,试图看出些花苞。
“我不擅花艺,在这会不过是随意剪两下子,附庸风雅罢了。”黛玉笑一笑,将那盆转个圈。是展示自己‘不擅此道’,却也叫博二夫人看清这作物长得多么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