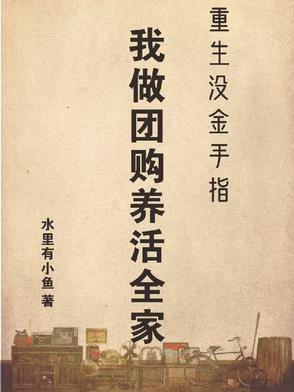无线文学>天命所归:观主在上 > 第202章 难道是哑巴(第1页)
第202章 难道是哑巴(第1页)
“咳、咳咳咳——”
喉头猛地一阵痒,叶亭猝不及防地咳了出来,声音在寂静中格外刺耳。
他躺在冰冷的地上,四肢像被抽空了力气,连眼皮都沉得惊人。本来带着的包早已不知所踪。
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,混杂着金属锈蚀的腥气。
他努力侧耳听着,耳边除了自己沉重的喘息声,还有某处传来轻微的动静——轻微的呼吸声,细碎的脚步,衣料摩擦墙面的声音,断断续续,若有似无。
看来,这里人还不少。
忽然,黑暗中传来一个声音,语调平淡,甚至带着点莫名的随意,“新来的,你几岁?”
那声音听起来很年轻,像是十几岁的少年,语气既不像挑衅,也不带关心,更像是在例行盘问——但那份毫无感情的淡漠,像针一样扎在神经上。
叶亭想开口,却现嗓子紧,只咳出了几声粗哑的气音。
周围一阵有气无力的轻笑声,不用刻意压低了声音说话都听不清内容,只能辨出多个音色:有的低沉、有的尖利。
叶亭的心沉了下去。
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。
在脑袋村的地下室,当时破开门时,看到的不就是这样的一副景象。
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响起。
叶亭勉强抬起眼皮,光线太暗,能分辨的只有一片晦暗中,一道瘦削的身影缓慢靠近。他下意识往后缩了缩,却被冰冷坚硬的墙角死死挡住。
“我问你,几岁?”
那人蹲在他身侧,嗓音不高,却有种与年纪不符的沉稳。
等半天不做声,他有些不耐烦,“难道是哑巴?”
叶亭艰难地咽了口唾沫,舌头仿佛也不听使唤。
他喘了几口气,终于艰涩地挤出几个字,“……二十。”
对方沉默了一下,忽然笑了,那笑声很轻,像刀子划过布帛,丝丝拉拉地透着诡异。
“跟我一样大。”那声音说,“难兄难弟。”
他自顾自地说,“我已经来了两天了,估计很快就轮到我了。好不容易死前能见一面,也算有缘,我叫佟年,你呢?”
“叶亭。咳、咳咳——”叶亭缓了缓才说,“为什么……我觉得全身使不上力气?”
“看样子,你也是被洒了粉迷晕了弄进来的?”佟年说,他抬手指了指几个方向,那里隐约躺着几个人,“那几个也和你一样,是被迷晕了扔进来的。估计他们的迷药里面有导致肌无力的成分。反正这几个扔进来到现在,一直都是那副死样,连坐起来都做不到。”
叶亭突然意识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
这……自己都已经筑基了,怎么还能被普通迷药放倒?
哇,不敢想象,如果活着出去,被恩人知道这档事,会死得多年轻。
“你还能挪动,所以你不是被迷晕的?”叶亭现在勉强能动动脑子和嘴。
“对,我更倒霉一些,被人一记手刀干晕了。”
“呲——听着就挺痛的。”
“你没看我现在还有点歪脖子的样子?”佟年侧一下头,一下子牵扯到痛的地方,疼得龇牙咧嘴。
“太暗了,看不清。”
“你刚来,还没适应这么黑的环境,正常。”
“你刚才说,很快轮到你了……轮到你干嘛?”
“被拖走啊。”
“拖去哪儿?”
“不知道,反正看到的都是半死不活地被拖走,没有回来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