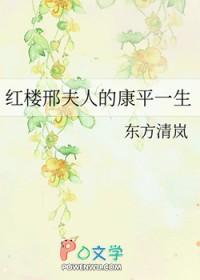无线文学>田园女神的逆袭甜宠记 > 第303章 争取村民推进信任(第1页)
第303章 争取村民推进信任(第1页)
晨光微露,我站在院中,手里握着一柄小铲子,在泥土里轻轻翻动。昨夜刚下过一场小雨,地面上还带着湿润的凉意。承安蹲在一旁,正用树枝拨弄一只慢悠悠爬行的蜗牛。
“妈妈,它背着房子走路,会不会很累?”他仰起头问我。
我笑了笑,蹲下来揉了揉他的头:“也许它习惯了。”
顾柏舟已经去田里了,今天要清理几块新翻的土地。昨晚我跟他说起今天的计划,他只是点点头,说了一句:“你想做就做吧。”语气平淡,却透着坚定的支持。
我明白,此前送米、熬粥只是铺垫,让村民亲自参与并收获成果,才是赢得长久信任的关键。
我站起身,拍了拍手上的泥,望向院子外的小路。今天是我第一次组织这样的“农事研讨会”,虽然谈不上正式,但至少得让大家愿意停下脚步,听我说几句。
“妈妈,有人来了!”承安忽然跳起来,指着门口喊道。
我转头一看,果然是林婶,她穿着那件洗得白的蓝布衣裳,手里拎着一个小竹篮,走得不紧不慢。走到院门口,她朝我点了点头,没说话,把篮子递了过来。
我接过篮子,心头一热。里面是几个鸡蛋,还有两根新鲜的青菜。
“你家吃点好的。”她说。
我笑着应了声:“谢谢林婶。”
她摆摆手,往院子里扫了一眼:“人都还没来吧?”
“还没呢。”我指了指院子中间搭好的简易讲台,“不过也不急,等他们有空了自然会来。”
林婶嗯了一声,走到一边坐下,顺手从口袋里掏出手帕,擦了擦椅子才坐下。她的动作让我想起上一辈人那种朴素又讲究的习惯。
不多时,陆续有人来了。有的是抱着孩子来的,有的是牵着鸡来的,也有几个汉子在门口探头探脑,最后还是进来了。人数不算多,但也够围成一个圈。
我站在讲台前,看着这些人,心里有些紧张。不是怕没人听我说话,而是怕我说的东西他们听不懂,或者觉得不值一提。
“各位乡亲,”我开口,声音不大,但在安静的院子里格外清晰,“我知道大家种地都不容易,尤其是这两年天灾不断,收成不好,大家都愁。”
人群中有人低声附和,也有人沉默不语。
“我想试试看,能不能教大家一些新的法子,让地里的粮食长得更好一点,产量高一点,虫害少一点。”
“你说的新法子,是不是那些奇怪的种子?”有个中年男人皱着眉头问。
我点点头:“是有一些特别的种子,但更重要的是怎么种。比如,什么时候该松土,什么时候该施肥,哪些作物能轮作,哪些不能混种……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学的。”
“说得轻巧,我们哪懂这些?”另一个妇人嘟囔着。
我嘴角上扬了一下,没有反驳,而是转身从旁边的木箱里取出一小袋种子,摊开在掌心:“这是我自己试种的一种谷种,抗虫害,生长期短。我已经种了一茬,你们看看。”
我从桌上拿起一株提前成熟的小谷苗,叶片翠绿,穗子饱满,粒粒分明。
“这……比我家地里长的好多了。”有人惊讶地说。
“这真是你种出来的?”那个中年男人也凑近了些。
我点头:“是啊,用的也不是什么神药,就是按照科学的方法管理。我可以教大家怎么选种、怎么播种、怎么照料,只要愿意学,都能种出来。”
院子里一时静了下来,大家都在琢磨我说的话。
林婶忽然站起来,开口道:“悦娘,我想试试。”